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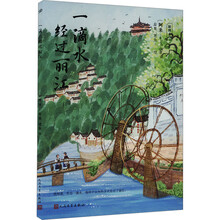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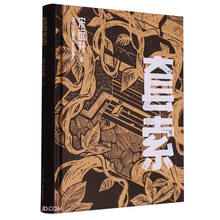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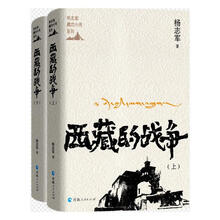
《2022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由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从2022年全国公开发表的数万篇微型小说沙里淘金,遴选出本年度代表微型小说创作水平的精品佳作。既有老一辈微型小说名家的力作,也有新一代作家特别是大学生写作者的佳作,作品内容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以小人物、小事件反映时代变化和社会生活。
路人老耿
笛 子
下午,老耿老两口下公交车往老表住的小区走去。
前面突然一阵人群骚动,夹杂着惊叫声。老耿快步走近,见两个男人在抢夺
一把 U 型铁锁。地上有个摔烂了的蛋糕,还有散落一地的苹果、梨。
打架的两个男人,一个五六十岁,高个块头大;另一个,瘦子,个矮且黑,
额上青筋暴突,眼神凶狠,抬脚狠踹。
围观群众喊“报警快报警”,还有人惊呼“要出人命了”。
围观的人只敢隔着一段距离大喊不要打,没人上前制止,怕被误伤,毕竟那把大号铁锁看着太吓人。
老耿见状就要冲上去,被老伴一把扯住:“危险,等警察来!”
“我就是……”
“不,你早退休了。”
老伴急忙掐断老耿的话,使劲扯住他的胳膊。
瘦矮个脸色铁青,豁出命的样子。大块头的脸渐渐憋成猪肝色,嘶声叫喊,眼睛不时望向围观者。
老耿迅速挣脱老伴的手,大喊“住手”,人已箭步飞至,右手闪电般抓住两人争抢的铁锁。
胶着状态的两人都怔了怔。大块头满脸的悲愤惊恐,喘个不停。
“不要打架,都放手!”
老耿说着去掰矮个的手,对面的手指钢条般紧紧钳住铁锁,掰不开。
老耿转去掰大块头的手,没想到轻轻一下就开了,似乎就等着有人来这么一下。
老耿挡在两人中间。直觉告诉他,此刻的矮个像个被点着导火索的炸药包,火苗虽已被他掐灭,但得防备复燃。
老耿对大块头说:“趁警察还没到,赶紧回家吧。不怕家里人担心吗?”
大块头愣了下,慢慢弯腰蹲下,捧起地上的蛋糕盒小心翼翼地摆弄着,试图把摔塌了的蛋糕复原。可哪能啊,他急红了眼,捧着蛋糕起身走了。背影里,能看到他不时抬起袖子在脸上揩一把。
“肥佬也真是的,买个苹果挑挑拣拣嫌七嫌八。”
“就是,都给他优惠了又说不够秤非要多拿一个走,他咋不干脆说不要钱送他吃?”
老耿从众人七嘴八舌中大概知道了事由:大块头买苹果为了多占便宜,说诈秤,把瘦矮个激怒了。
“唉,这肥叔住我同个小区,无儿无女,他老伴常年生病,钱大多去买了药。刚听他说今天生日,蛋糕是开甜品店的侄子送的。”
旁边一大姐说完,现场又一阵静默。
大块头的处境令人心酸,老耿更为瘦矮个担心。刚才在掰手时,发现他手背有两道刀砍疤痕。凭职业经验,这绝不是一般的伤。
此刻瘦子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脸沮丧和茫然。
老耿蹲下来捡起地上磕出了大小不一“瘀伤”的水果。老伴和旁边的两位大妈也加入到捡果行列。
跟大块头同楼的大姐忍不住说瘦子:“还好这位阿叔出来劝,不然都不知后果怎样,我现在心还怦怦跳啊。”
“我最恨别人冤枉我,说我诈秤。”瘦矮个恨恨道。
“那也不要把人蛋糕砸了啊,他多难得才吃一次蛋糕,看他都快气疯了,我刚才真担心你会被他用锁砸死。”
“砸死最好!”瘦矮个像在跟谁赌气。
“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大男人没点家庭责任感。有为老婆孩子想过吗?死死死的!”老耿的老伴把刚才受到的惊吓完全置换成愤怒,狠狠砸给瘦子。
“我没老婆,早跑啦!”
呃!她像喝水被呛到,咳了起来。又从车上扯下一个塑料袋,把磕得惨不忍睹的苹果、梨捡进袋子,装到不能再装,然后放到电子秤上说:“多少钱一斤你说了算,我可以买回家做苹果饼。”
又有两个人跟着去扯塑料袋,有的捡苹果,有的装梨子。
阿婆大妈们听到他老婆跟人跑了,纷纷动了恻隐之心,个个把袋子装得不能再装为止。
见此情景,矮个竟喉咙发紧,话里带着浓重的鼻音:“这些苹果、梨摔到很难卖得出去,多谢大家不嫌弃。”他坚决只收半价的钱。
“是我自己的错,怪不得别人。”瘦矮个见老耿盯着他手背上的刀疤看,又下意识地缩了缩手,像在自言自语,“我以后会想想后果,再不会随便动怒了。”
今晚的老耿很开心。他给自己和老伴倒上小半杯红酒。
“不喝,你高兴我不高兴。死老头子,为你担惊受怕了二三十年还不够,好不容易熬到你退休,以为可以安心了。”
老耿赶紧哄起来,他把酒杯举到老伴面前:“我今天阻止了一场悲剧,高兴啊!有你的功劳,来,老头敬你。”
老伴不再绷脸,接过酒杯放一边,严肃地盯着老耿的眼睛,要他保证今后不再做冒险的事:“毕竟是退休的人了,要服老啊。”
老耿嗯嗯嗯地点头如捣蒜。
老伴丢给他一个白眼。她知道答应了也白搭,下次遇到这类情况,老头子还是会不要命地冲上去的。
“那人绝望的哀号让我整整三天没能睡好哪。”老耿又说起他当警察的往事,“以前,有个死刑犯,曾当着我的面痛哭流涕地忏悔,说当时打架是一时冲动昏了头,如果当时有个人上来干预一把,也许悲剧就能避免。他哭着说,可惜我命中没有贵人啊……”
这次老伴没有嫌弃,任由他说。等他说完,再给他递上一条热毛巾。
泥蛋糕
曾 颖
灵儿觉得自己长大,是在她十岁生日那天。
那天,爸爸妈妈连电话都没打一个回来,只有奶奶临出门时把一个煮鸡蛋放在她的书包里—这是山里娃们生日的标配,也是与平日唯一不同的地方。
走在上学路上,灵儿的心,从没有过地凉。平时就崎岖而漫长的路,找碴儿似的变得更加腻滑。她眼前总闪过电视上城里孩子过生日的画面,一大群欢快的人和精美的礼物,围着那个满脸幸福的孩子,点蜡烛,唱歌,切蛋糕,欢笑……
灵儿不敢将自己想象成那个孩子。她只希望自己生日这一天,爸爸妈妈能回来,如果再带一件新衣服或一套彩色铅笔,或者一个蛋糕,哪怕是最小最小的那种,她都会高兴得疯掉。
但这些场景,如同卖火柴的小姑娘划起的火光中的幻影,瞬间就被一次滑倒撞得烟消云散。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奶奶常说的那句话:“东想西想,吃了不长,我们这样的人,做梦除了伤自己,就再没有别的用处了!”
奶奶这句话,是针对爸爸妈妈外出打工说的,但此时此刻用在自己头上,却十分贴切。坐在湿滑的地面上,一股沁骨的凉意,由下而上,让她的每根头发尖里,都充满了沮丧。
学校和家,都一样遥远,她两头都不想去,不想让奶奶和她唯一的同班同学,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于是她索性站起来,往路旁树丛中的小道走去。这条道她见过几百遍了,通往哪,她并不知道。
穿过竹丛,沿着一条不太明显的小道往前,是一条小溪,小溪往上一百米,便是一处并不太深的小潭。
周围是树,并没什么人,她决定去那边把裤子洗洗,晒干再说。
裤子洗好,晾晒在小树上,她选一块石头坐下,把脚放进水里。
水凉凉的,沙软软的,偶尔有小鱼银亮亮地从她的脚边穿过,风柔柔地由远及近,抚过竹枝和树巅,把一丝丝山林的清香,铺洒在她的头上和脸上。
她闭上眼,用力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呼了出去,仿佛要把一切的不愉快,都吐出去。
这时,半空中,缥缥缈缈传来许多人的欢笑,有人开始唱生日快乐歌,杂乱的笑闹,被他一带,变得整齐高亢,在树和山之间飘荡回旋,如一群欢快的鸽子。
她知道这是那个害她摔跤的梦的延续,她本能地摇头,想把它们驱散。但歌声像一群顽皮的蚊子,你一驱,它就散;你一停手,它就又聚在一起,还故意使坏地唱得更响。
努力了几次,她决定放弃。
偶尔做一次过生日的梦,应该不算过分吧?
她这么想着,突然就来了精神。她决定再把梦做大一点,给自己做个生日蛋糕。
河边被水泡得软软的黄泥,倒是做蛋糕的好材料。她挖了一大捧,放到一大片芋子叶上。用黄泥和菜叶做饭菜办过家家玩,是熟悉而久远了的游戏。而用它做蛋糕,还是头一次。蛋糕在电视和书上看到过,知道它是圆圆的,表面是白色或棕黄色,顶层有各种水果和糖球,还有写着漂亮文字的卡片。
这些东西的替代品,都不难找。黄泥做蛋糕坯,石灰做奶油,树上的野山桃,田里的小番茄,崖壁上的青花椒,还有小溪里的石头,白色的青色的红色的,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放在生日蛋糕上,像有生命一般地鲜活美丽起来。
蛋糕做完,放到阳光下,虽然漂亮,但又感觉像少了点什么。对,卡片,还需要一张写了字的卡片!
她从书包里拿出平时不怎么舍得用的水彩笔,撕下一片软面抄的封面,在上面认认真真地写下几个字:
祝我生日快乐 !
这时,整个山林,都唱起歌来。
歌声由弱到强,由悠扬到高亢,直至如漫天的大火,一直烧上云霄。
她觉得,从那一刻起,她已不再是个孩子。虽然此前很久,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早已不把她当成一个孩子。
她把蛋糕放到山崖的一棵树下,像放一个祭品,提起裤子,背起书包,大踏步往山下走去。
在学校的路口,她看到她唯一的同班同学和同桌,那个老是上课嚼米的小男生,手里捧着一个烤红薯,红薯上插了支小红蜡烛,远远看到她,欲言又止。
她知道那是送给她的。
如果是两小时之前,她会感动得眼泪哗哗的。但现在却不会了,因为她不想再为了一个别人随时都可以吃到的小蛋糕,感动得昏天黑地,她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是多年后一个叫娜娜的陪酒女酒醉之后向客人讲的她朋友的童年故事。
但大多数人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