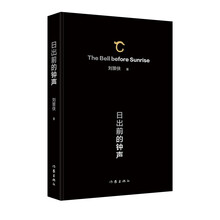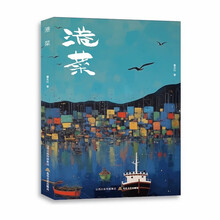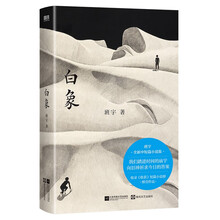第一章
林蔚第一次进我家门是在1925年。那年,我爷爷年二十一,刚刚与我奶奶成婚。那时,我家即在宁溪山区的半山村。半山村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小山村,全村六百多户,一千多口人。所有的房子,全建在大裂谷的半山上。一条长长的小溪,从高处流下,哗啦啦地笑着、唱着,银蛇似的蜿蜒着从村子正中间穿过。我家的房子,即坐落在日夜不停喧嚣的小山溪旁。尽管我离开半山村多年,但我家的那座石头砌成的老房子,一直保持着初建时的原貌。每每十月金秋,半山村的橘子黄了,柿子红了。那橘子,黄得如星星点灯,在明媚的阳光下不断地抢着游人们的一双双眼睛,让人深感赏心悦目;那柿子,活似一盏盏红灯笼,高高悬挂在软软的枝头上,让人感觉到人与秋天没完没了地举行“婚礼”。站在大裂谷山顶处,往半山村俯瞰,一排排明墙黑瓦错落有致,房与房之间,株株绿树四下点缀,无一处不是恰到好处。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无论你怎么看,都如一座放大了的盆景。从平处看我老家半山村,给你的感受更是别具一格。九曲回廊,巷深街幽,一家离去一家迎。“青山绕路曲八九,流水趁桥盘两三。欲识松风半松月,须凭亭北与亭南”,正因如是,难怪我的表妹——半山村党支部书记许山英,每次来我家,都对我感叹说:“哥,我感谢你。是你让我选择归乡创业。外面龙窝,不如家里狗窝。家乡好啊,家乡好得人不老;家乡好得青山绿水,即是黄金元宝。”
2018年10月11日,我的同窗好友们集体决定去我老家拥抱亲吻半山古村。那天,我正坐在书房中看书,他们齐崭崭地走进我的书房对我说:“我们知道那里是你老家,那里岩头鹘见了你都不飞。我们打算去你老家玩一次,你陪我们去玩一玩好不好?”说实话,我内心一直在去与不去的边界上徘徊。不想去,那是假的。家乡是土地,家族是家乡土地上的一棵树。哪个中国家庭,不是百家树中的一根枝条?哪个人又不是百家树中的一片叶子?哪个人的心头,又没有家乡情结?那股浓郁的家乡情结,哪天不似一条红丝线一样紧缠他的心头?
说去,我真就说不清道不明是因何种原因,一直不敢直面我家乡的山山水水。是因我太多亲人在那块土地上死去?还是我本人欠半山村太多的感情债?斩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令我挥之不去,又不敢面对。我犹豫片刻,最后,我还是决定陪着好友们去我老家走一趟。
那天,他们在我家按下他们共同想好了的时间确认键。
那天,他们在我家确认了车子的分配方案。
那天,他们离开我的家。他们是离开了。可我原本沉淀在盆底的记忆淀粉,全被他们的举动搅成一盆黏稠的面糊了。我不得不用记忆的勺子,将他们一勺勺地□(特殊字体)上来,在黑色油亮的平底锅上,摊成一张张两面焦黄的煎饼。 我想起我家那高高的南征顶山。那南征顶山活似一柄宝剑直插云霄。那山最美的景色,则是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时呈现出来的夜景。那长长的峡谷两边高山壁立。喋喋不休的山溪水,若一条银色的鳗鱼,蜿蜒着身子在深深的峡谷中流淌。那遒劲的老藤,有如悬崖峭壁上编织成一道军事防伪网。成群结队的蝙蝠“扑簌簌”地在那绿色防伪网中来回穿梭。银盆似的大月亮,一动不动地钉在峡谷中间。只要你细细瞧它一眼,那夜景遂将你带入幽冥的梦幻世界。
我想起我老家山上的“岩头鹘”与“铁子松”。岩头鹘是我老家生长于山中的猛禽,它的真实名字应当叫山鹰。岩头鹘最大的优点,即是集信、义、警、敏、勇、诚,恩冤分明以明世。说信,它死守着上苍给予的食物链,专食山中繁殖量最大的山鼠与野兔;说义,鹘与鹘之间互相抱团儿取暖,不舍不弃;说警,它的目光锐利如刀锋,能在千米外看清地上躐蹄着的山鼠和野兔;说敏,它扑簌着翅膀下来,爪一伸,即可将猎物一把抓到手;说勇,它没有恐惧,没有胆怯,哪怕是天风怒号,乌云似战车在沙场驰骋,它照飞不误;说诚,它有仇必报,有恩必还。由于它的天敌是蛇,图防蛇,它不得不将巢筑在那高塔或悬崖峭壁的松树上。正因如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岩头鹘”。
铁子松,是由松树种子掉在悬崖峭壁隙缝中长出来的小松树。初时,有那么一颗松树种子,或是由风吹着,或是由鸟嘴衔着,偶尔掉入壁立的岩缝中。也许弥漫着的山雾对它有所滋润,也许上天的雨水浇淋让它内蕴着的生命力量得以复苏,于是小小的芽尖冲破坚硬的盔甲,绽出一株米星般大小的嫩芽。无论是植物还是人,图生存,它的意志即会变得钢铁般坚强,丝绸般柔韧。于是,那小小的须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顺着山的褶皱蜈蚣腿般延伸下来,一直延至山脚,长达百米,一旦它的须根与山麓下的泥土接触,即会一头扎入土地的腹部,从大地的肚腩中汲取它必须汲取的养料;不管遭遇多大的天灾人祸,不屈不挠地让自己在石壁上生存下来。一棵碗口粗的铁子松,从出芽长成手臂粗的树身,起码得有上百圈细密的年轮。别看铁子松树小,灾难令它坚韧异常。一般的锯子与刀子很难将它锯开与砍断。做成的家具,重得如钢浇铁铸不说,千年百年不变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