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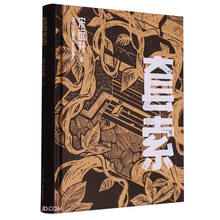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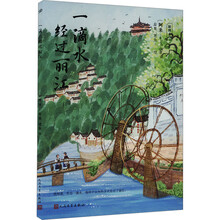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该作品是一部充斥着强烈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中国北方农民家族史诗长篇。作品以八年抗战时期为主要背景,讲述了同是数百年前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到穆刀沟边讨生活的南北穆家人,因为利益冲突结下世代仇怨,争斗不休。日军来到穆刀沟后,占田地,杀亲人,糟蹋女人……河两岸的穆家人毅然摈弃前嫌,笑泯恩仇,认祖归宗,携手一致抗敌,以一具具血肉之躯谱写出一曲民众自发抗战的浩然长歌。小说生动地描绘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展示了民众揭竿而起自发抗战的感人情景和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内涵丰富,有着史诗性的纵深感,再加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因此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和认识价值。
引 子
谚语说:冰火不同炉。
疯子爷和瞎子爷乃同一个人,他既是疯子又是瞎子。贾先生说,唵,这世上呀,疯子才是明白人,世上的事儿,也只有瞎子才看得清。可没人认同贾先生的胡言乱语,正如没人相信疯子爷的疯言疯语,听者顶多咂咂嘴,报之以残花似的一笑。
苦命的疯子好多年前曾失踪过,据说出走时有人见他上了河岸,坐在岸上哭骂一天一夜,直骂得脸红了的太阳逃遁到山后,黯然失色的夜空星稀月落,风也哭泣起来。他骂天骂地,更骂身边的河。哭骂过,他起身离去了,一路逢人便说:这河里流淌的不是河水,而是一河黄色的沙。
一条九曲十弯的地上河流过无极地界,像条黄色飘带悬挂在北方的原野。河床时窄时宽,窄处人站岸上可隔河说话,宽处一眼望去却不见对岸。先民们最初管它叫“河沟子”,直到宋朝末年才有了个“穆刀沟”的名号;待它流进大清国,也落脚在了官府的图册上,在河流家族里归了宗,谓之“木刀沟”。一字之变有些微妙。妙在何处?有解却又无解。不过,河边的汉人并不买满人的账,乡间仍固执地坚守原来的称谓。
只是不承想,这本寂寂无名的“沟”上了大清国的河流志,可就大大出名了。出的是恶名。
课雨占晴费运筹,
雨多河涨又堪忧。
滋川滹水犹其后,
为患先防木刀沟。
还是清同治十一年,面对这恶名远扬的河流,亲民知县寿颐大人写下首诗,继而亲率治下子民挖河固堤,却也于光绪三年叹声“奈何”,黯然而去。自此他再没回来,正如后来离去的大清国再没回来。
人们无法读懂这河流,就像无法读懂这河边的人。这河说不定会在哪年的夏秋季节里突然怒发冲冠,凶神恶煞般狂暴地越过河堤,汹涌泛滥,淹没两岸平缓而肥沃的土地,然后扬着淡漠的面孔,无声地退回深深浅浅的河床,退守大北方著名的白洋淀里,身后留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茫茫白沙。
河两岸原是白狄人的故地——中山国。自从白狄人灭国,河边也就住上了一个农耕民族——早期称“华夏人”的汉人,之后内忧外患粉墨登场,河水冲积的这片平原也就有了数不清的灾难。自此,那富足而祥和的日子也就远去了。漫长的岁月里,平原上不时狼烟弥漫,尸横遍野,流淌的河水也散发出血腥的味道;待到“燕王扫北”后的“靖难之役”——“红虫之灾”,这平原上就几乎没了人烟。平原荒芜了,只是几年后,人们才陆陆续续从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下迁来,平原又一次有了人间的样子。
一个草黄木枯的秋天,一拨拨被捆住双手的洪洞人——像一群群疲惫的牲畜,被兵丁差役押解过太行山,走在异乡的路上,到了冀中平原。他们艰难地走着,耳畔似乎铜锣的余音未绝,官府大老爷的训话声仿佛依旧在耳边缭绕——“到了山那边,就有好日子了……”
与众多无助的乡亲一样,一对穆姓兄弟被丢到了真定府地界。偶尔,兄弟俩在幸存下来的原居民口中听说了“穆刀沟”的名字,禁不住一阵激动,随即寻了过来,停脚在穆刀沟南岸。
两人穿行过没腰深的荒草,依稀可见那委之于地的残垣断壁犹如影迹——像是还沉浸在野草下古老而忧伤的沉思里。两兄弟定居下来,娶妻生子,开枝散叶,过了数十年,繁衍出了两个血脉相连的家族,也就形成了个家族村庄。村子自然而然有了名字:穆家。
好日子似乎真的来了。只可惜,这世上最难办的事就是人的共存,哪怕是兄弟。
若干年后,不幸祸起萧墙,两个家族就像变天一样翻了脸,而且势同水火。弱势一支无奈之下迁走了,在一个秋末,迁到了北岸那片风沙弥漫的荒野。那片茫茫荒野,仿佛只有零星的荆丛或稀疏的野草在昭示着生命的存在。又是几代过后,北岸家族才壮大起来,那片荒芜已久的贫瘠土地也种成了沃土。
自此,人称北岸的村落为北穆家,南岸村落为南穆家。南北穆家隔河相望,这一望,就望出了世仇。
仇恨出疯子。说来奇怪,大概自南北穆家人生出仇隙,疯症的基因也便在穆家人的血液里发作起来,一发不可收拾。由此说到穆家,外界流传着一个说法:世世不和睦,辈辈出疯子。可穆家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世上,疯子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哩?谁又不是疯子哩?难道你不是?
人世间热衷于堆积仇恨,也在堆积着罪恶。穆刀沟日夜哼唱着忧郁或愤怒的歌声,流过冀中,流过平原,流淌着两个同血脉家族的恩恩怨怨,流淌着那些恩恩怨怨编织的苍凉、沉重和忧郁的故事。那些故事——犹如战乱时的河流,也带有血腥的味道。
第一章
谚语说:两兄弟,分了家,耗子都不准过界。
一
当嘶鸣的北风将晨色从幽夜里吆喝出来,黄历也翻到了民国二十 三年正月十五。这天,南北穆家的对台戏又将上演。两个家族都铆足了劲儿,摩拳擦掌,隔河以待,蓄势新的一回全力一搏。
虽已过立春,可冬日的寒冷依旧野蛮地统治着北方。天亮了,满腹心事的老天郁郁寡欢,目光阴沉、呆滞;大地被有些发灰了的残雪覆盖着,显得空旷、清冷、落寞,甚至荒凉。趾高气扬的风还在刮着,吹着尖厉的口哨打河岸掠过,岸边枯瘦的老槐树瑟瑟发抖,柔弱的岸柳惊慌地甩起纤长的枝条,发出“嗖嗖”的尖叫声。然而,沉睡的河流仍然沉浸在一个自我的幻梦里,像是世上的一切声音都无法把它吵醒。
寒风撩开了早晨的雾纱。远远看去,有个黑点静止在穆刀沟里,似乎冻结在了泛着翡翠色光亮的冰面上。近了发现,是个蹲着的半大孩子。半大孩子佝偻着身子,背对着寒风,半个头缩在袄领子里,一动不动。风一阵阵在他肩头掠过,冷言厉色地说着恫吓的话语。直到晨后,风像是终于累了,这才有气无力地慢慢安静了下来。
半大孩子突然动了。
他面前是个瓮口大的冰窟窿。他开始一把一把轻轻倒手,从冰窟窿里往外拉拽绳子,绳子那头是条还在挣扎的鲤鱼。鱼有一尺长,是他今天钓到的最大的一条。
他把鱼扔进荆条篓子,那鱼跳了几跳,篓子在轻轻晃动中发出一阵“噼啪”声响。他站起身来,长长出了口气。大概蹲卧的缘故,黑粗布裤腿弯成了弓形,膝盖肿胀似的发亮。他仰了仰黑土色而带些冷漠的脸——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眯起的眼睛小得有点过分,像两条细缝儿。人们管这类眼睛叫“眯眯眼”。“眯眯眼”名叫腊八,家人这么叫他,外人则叫他“疯子腊八”或“疯子”。自从他把杀猪刀子插到那老中医的柜台上,老中医悄悄对人说“这孩子得了疯症”,他就成了疯子。
疯子腊八像是受了风寒,咳了一声,白色气体从嘴和鼻孔里喷出来,接着,两股带怨意的清鼻涕郁郁地流进了嘴里。他伸出指头捏住冻红的鼻子,“噗”的一声擤了把鼻涕,手胡乱在袄襟上抹了抹。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回头往北方看了一眼。说来也巧——正如他所料,此时恰有一个人出现在了河的北岸上。
走上岸的是穆大脑袋。大脑袋与疯子腊八年龄相仿,却长了个门楼状大头,因此走起路来总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人们说长了大门楼头的人聪明,可也有尖酸刻薄的人背后开涮说:聪明不聪明也就那样儿,可他脑袋也忒大了吧,都要把脖子压折了!就是走道儿——兴许人还没见,额头就撞墙上了!
大脑袋在岸上站了一会儿,迟疑地走下河来。在靠近河岸的地方,他撂下筐子,又向这边望了望,开始凿冰。他两腿微微叉开,双手握着锨柄一下一下凿着,并不时朝这边偷窥上一眼,那情形,活像个小贼在偷东西。大脑袋发现,疯子腊八终于还是朝他走了过来。他停了停,想离开,可又有些不甘,踌躇了一阵最终还是决意留下,只是凿冰的动作放缓了——有些有气无力似的。直到腊八眯着小眼睛在他面前站下,他也就像得到命令似的住了手,站直了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