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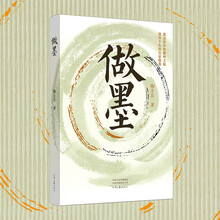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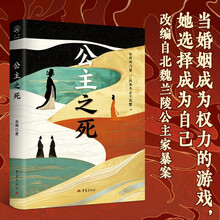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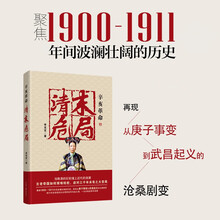





第一章 名门之后
一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冬天,江陵府。
北风如刀,削得满山黄叶尽落,地上只剩断筋枯草。江陵府衙大院里,两个年轻人眉头紧锁面如霜结,显然是遇到了一件极其为难的事。
年纪较轻,个头却要高上一截的年轻人说:“要不,先瞒着先生吧?”
另一个年轻人叹了一口气,说:“你我都不善说谎,先生又那么精明,我们怎么瞒得过他?再说了,就算侥幸瞒过初一,十五怎么办?”
说话的两人是师兄弟,师兄叫陆岭,师弟叫陈齐一两人正准备去见老师张拭。
陆岭说完,把手里握着的一封信收入宽袖,又仔细掖了掖,确定已经把信藏好,这才迈步向张拭的房间走去。
陈齐对陆岭的自作主张有些不满,待在原地没动。等陆岭走到了十步开外,才举步向他追去。他人高腿长,走得又急,很快后来居上,反而走到了陆岭前面。
北风更急了,天空也越来越阴沉,两个年轻人的手冻得通红却浑然不知,远远望去,像是四朵红梅,摇曳于朔风之中,有些凄艳,有些落寞,更有些不知所归。
卧房内,张拭正用左手撑着桌子,给弟弟张构写信。手中的兔毫仿佛重若千钧,每写完一个字,他都要停下休息一番。等拖完最后一笔,张拭再也承受不住身体的沉重,又摸回床上重新躺下。
自从夫人宇文绍娟死后,张拭的身体便每况愈下;此后领镇静江,日夜忙于政务,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他曾多次上书皇帝,希望能准许他告老还乡。皇帝不仅不许,还在今年派他知江陵。
张拭的性格使他无法尸位素餐,明知身体不佳,到任后还是马不停蹄地缉强盗,去贪官,抚百姓,兴庠学……事事亲为,劳心劳形。
让人忧愁的是,尽管他全力治贪,曾一口气参掉十四名贪官;官场的贪腐之风,却没能得到根本的遏制。他重视教化,经常亲自给学子们讲学,勉励他们以后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远涉江湖,都要以忠君报国为念;可学子们,却一心向着功名。
百姓疾苦,官员们却耽于享乐;金虏未灭,学子们渴望的却只是拜相封侯的实惠和风光……整个江陵,乃至整个大宋,就像一艘破船,船上之人不仅不去堵塞漏洞,反而盼着樯倾楫摧的那天,好抽去几块船板!
外劳内忧,张拭病倒了。他自知大限将至,凝思数日后,于一个深夜提起兔毫,用最后一腔热血化开浓墨,写下一道奏表,劝诫皇帝不忘靖康之耻,肃清内政,为北伐复国打下基础一张拭尤其提醒皇帝,用人要合乎天理,不能只顾自己好恶,以致小人得志,贤人去国。
奏表送入京城,却像将一块石子,扔进深不可测的峡谷,至今仍未听到那落地之声。
张拭感到自己也像是站在万丈峡谷之侧,随时可能坠入无尽的黑暗和虚空之中……
将近张拭卧房,陈齐拦住了陆岭:“再考虑一下吧,先生肯定受不了这个刺激。”
陆岭仍坚持己见。两人陷入争辩,声音不觉大了起来。
浅睡的张拭被二人惊醒,说:“是陆岭和陈齐吗?都进来吧。”
陆岭和陈齐大声应了一声“是”,轻轻推开了房门。两人看见张拭半靠在床上,胸脯起伏,嘴唇翕动,苍白的双颊含着一抹病态的晕红。
陈齐心中一紧:先生的病,看来是更重了。
“你们在外面嚷嚷什么?”
虽在病中,张拭仍有一股威严。陆岭和陈齐不敢看他,都垂下了头。张拭无暇教育弟子,他心中最为挂念的,还是那件大事:“有消息吗?”陆岭、陈齐互看一眼,都没有回答。
“说话呀!”张拭又急又怒。
“有!”回答的却是陈齐。
听了这肯定的回答,张拭胸口突突狂跳,一口气不顺,竟无力说话,只好用目光示意陈齐说下去。
陈齐却不知如何开口。
陆岭见状,赶紧上前一步,说:“子寿兄来信说,奏折没能送到圣上手里……”
子寿指的是张拭弟子彭龟年,他做了一任地方官,回朝廷述职,目前正在临安。
“啊?为……为什么?”
这一下,就连陆岭也语塞了。
张拭知道其中必有重大缘故,反而镇定下来:“放心吧,为师承受得了。”
“奏折被李公公拦住了,没能送到圣上手里……”
李公公指的是内侍李珂,他是当朝皇帝赵昚最宠幸的一位太监。
陆岭一边说,一边从袖中取出信件递给张拭。张拭只看了几行字,便感到有人朝他堆满火药的胸腔,扔下了一束火苗,接着便是一阵摧肝裂肺的爆炸……张拭只感到喉头又热又甜,终于“哇”的一声,狂喷一口鲜血,雪白的蚊帐顿时被血雨冲得一片狼藉。
“先生!”陈齐、陆岭拥到床前,又是抚背,又是用衣袖擦拭他胸前、唇边的血迹。
想到可能再也等不来皇帝的朱批,张拭万念俱灰,一把推开了两位学生。
陆岭赶紧劝说:“先生,您一定要保重身体,莫中了小人的奸计!只要您贵体安康,圣上迟早会明白您的忠心与苦心。若能提拔您执掌中枢,到时候就能和圣上一道,起贤斥奸,修内政、攘外敌,建千古不灭之功业,立万世不朽之英名!”
陆岭这番话,如果是以前,张拭一定很乐意听;现在却觉得虚假中夹着讥讽,听来字字刺心。
过度兴奋后的疲倦,希望落空后的幻灭,让张拭疲累已极,再也不愿说话。等弟子伺候他换过带血的被褥衣服,才再度开口:“你们忙去吧,晚上不用来伺候了。”
陈齐着急说:“先生,还是让我陪着您吧!”
“不用了,有什么事我会叫你们的。”
“那,我让冯叔把饭送到您房间?”
张拭此时哪还有心饮食?但如果驳弟子之意,又怕他们继续“纠缠”一于是,点了点头。
二
陈齐口中的“冯叔”,张拭叫他“老冯”。
老冯是张家一名老仆,比张拭大十多岁,从张拭出生之日起,就一直跟着他。两人名分上是主仆,张拭内心却视他为半个兄长。
弟子走后,张拭想睡一会儿,内心却思潮如涌,不但不能入眠,脑子反而越来越清晰。张拭感到心里有好多话一和平常说的话很不一样的话,想找一个人倾诉;却又担心这些话说出来,不仅会吓到别人,更会吓到自己。
老冯端着食盒进入房间,张拭见他披了一身雪,吃了一惊:“下雪了?”
老冯一边拂掉肩头的落雪,一边回答:“是的主子,下得好大。”
张拭莫名有些兴奋,撩被就要下床。老冯赶紧上前给他披上外衣,扶他走到窗前,并卷起了窗帘。张拭隔窗一看,只见漫天飞琼乱舞,就像千树万树的梨花,卷落于癫狂的北风之中。
张拭一脸兴奋地吩咐:“老冯,麻烦你再去烫一壶酒。”
“主子,你的身体……”
张拭摆摆手,说:“不碍事。”
不一会儿,老冯烫来了酒,又拿出食盒里的菜一一摆好。屋内烧着炭火,温度不低,饭菜依然温热。
张拭说:“难得大雪,陪我喝一杯吧。”
几十年来,只要是私己之地,张拭和老冯,就没有严守主仆名分。
老冯依言坐下,替张拭和自己斟酒,有意都没斟满。
张拭喝了一口酒,问:“老冯,你是哪年到的我们家?”
“建炎三年(1129)。”老冯看了一眼张拭,见他没有接话,继续说,“靖康二年(1127),金兵破了开封城,我随父母南逃。路上,父亲被金人杀死。我和母亲逃到寿春,被知寿春府事邓绍密收留。建炎三年,母亲和邓府君一家,惨死于范琼之手,只有我逃出生天,去临安找到了老主子……”
老冯口中的“老主子”,指的是张拭父亲张浚。
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老冯想起当年范琼屠杀寿春官民时的惨绝,仍心有余悸,端着酒杯的手也抖了两抖;好在酒未斟满,这才没有抛洒出来。
“后来,我父亲杀了范琼,替你母亲报了仇。”说到这里,张拭嘴角闪过一丝苦笑,“记得小时候,我见你祭奠父母,哭得很伤心,于是安慰你说:‘我父亲杀了范琼,替你母亲报了仇;以后我要杀光金虏,给你父亲报仇,给我大宋报仇!’唉,年幼不知天高地厚,何其狂妄可笑!”
老冯忙劝说:“主子莫要灰心,你正当壮年,等病一好,就有机会实现当年的抱负……”
张拭一声长叹:“满朝文恬武嬉,士子心中又只有功名,哪还有什么机会?”张拭最担心的,还是皇帝。
其时在位的是宋孝宗赵昚。登基不久,赵昚就起用张拭父亲张浚,发动了一次北伐。开始用兵顺利,宋军接连收复灵璧、虹县等地。后来遭遇金兵优势兵力反扑,加上主将李显忠和邵宏渊不和,以致大败于符离。
主和派大臣汤思退,联合太上皇赵构,不断给赵昚施加压力;赵昚本就性格犹豫,重重压力之下,很快便派人赴金营议和。
经此一败,赵春雄心大挫,虽然后来多次声称要再度起兵北伐,内心其实极为摇摆;加之官吏腐败导致民变蜂起,赵春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北伐?
近些年,因为用人不当,天下更加糜烂;别说北伐复国,能否图存,都已成问题!
张拭又想起那被宵小挡住的奏折,心中悲苦,仰头喝光了杯中酒,同时转换了话题:“复之还没有消息?”
复之,指的是老冯的儿子冯志。
老冯摆了摆头,没有说话;那干瘦又发量稀疏的头颅,就像一棵只剩枯枝残叶的老树。
冯志是老冯唯一的儿子,比张拭儿子张焯大五岁。张拭教张焯读书时,常常也会喊上冯志。因此,冯志虽是仆人之子,却也满腹诗书。
五年前,冯志州试落第;更让人奇怪和伤心的是:他竟然从此失去了踪影!老冯之妻李氏,思念儿子成疾,不到两年就撒手人寰。
五年来,老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儿子,张拭也让下属和弟子四处打探。传回来的消息很多:有说冯志受不了落第的刺激,投了长江;有说冯志被山贼掳掠,不得已做了山大王的军师——甚至还有消息说,冯志流落到了金国……
这些消息,真假难辨;老冯心里,也就忧喜并杂。然而,随着年深月久,老冯心底那丝希望之火,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微弱。
老冯本想劝张拭少饮几杯,听他提起冯志,心中悲苦,不禁和他一杯杯对饮起来。北风一阵阵叩击着门窗,似乎也是心有块垒,无处宣泄,只能拿这坚硬的门窗出气。
张拭酒量本不错,但因久病之故,几杯下肚,已经微有醉意。蒙胧的醉眼里,已经六十岁的老冯皱纹密集,目光空洞,看起来更显苍老。
张拭鼻子一酸,感慨说:“如果以前,我不严苛地要求昭然和复之读书做人,他们或许就不会,一个不到三十就长辞于世,一个一去五年了无音讯。你我主仆,也不至于如此老境凄惶……”
张焯字昭然。
老冯从没见过张拭如此颓唐,更是第一次听他否定读书明理,吃惊地看着他,说:“主子……”声音喑哑,如同含着一口沙。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北风更加愤怒地拍打着门窗,似乎里面的人和它有血海深仇,它又偏偏不得其门而入。冤屈和狂暴,让它一遍又一遍地退回、蓄力、出击、冲撞……却始终劳而无功。
张拭突然想到,小时候想杀尽金虏,替老冯报家仇。几十年后,非但没有替他报仇,反而因为自己,逼走他的儿子,气死他的老妻——这,岂不是给他制造了新的家仇?
苍天可鉴,他张拭从没想过要害老冯一家。
既然不是存心加害,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莫非,他一生上下求索、笃定不疑的大道天理,竟然——有问题?!
北风愤怒的呜咽声里,张拭仿佛听到了张焯、冯志的哀叹,千百弟子的苦吟,万千百姓的悲泣,山河将碎的哭号;也听到了王公大臣苟安的祷告,百官宴前的笙箫,小人志得意满的狂笑……
张拭感到胸中憋闷无比,直想用利刃剖开胸腔以释重压!他倏然起立,径直扑向了卧房门。
“主子,外面风大!”老冯赶紧起身相劝。
张拭却不顾老冯劝阻,一把扯开了大门。
暴雪挡住了视线,暴风吹迷了眼睛,张拭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快意:这不堪的世界,圣贤的教诲指引不了,君子的努力挽救不得,百姓的血泪洗涤不尽——那么,就让这狂风暴雪,将它彻底掩埋吧!
然而,真的掩埋得了吗?
不说其他,光是那几十年的旧事,就像一股股激流,冲破满地的积雪,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第一章 名门之后 001
第二章 狼狈天涯 048
第三章 蜀地之行 088
第四章 君臣之契 133
第五章 符离师溃 169
第六章 张朱会讲 194
第七章 治道之争 250
第八章 知行互发 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