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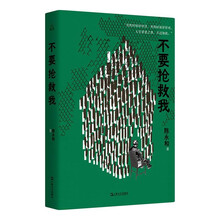




“原来这座城市是这样建起来的,
原来世间的每一座城市都是这样建起来的。”
十四个章节排布为巨型的诗行,组成十四行诗般的长篇小说。
继《山魈考残编》之后,原创作者黎幺又一部力作。延续其对世界与文本的思考,借瑰丽的语言与历史的碎片,形成的一部关于“元世界”或“伪元世界”的小说。
纷繁的历史在阅读般的写作中,被重新写成悖论般的、仿佛多刺的晶体的史诗。速朽的王权或世界的影子中,诞出永生的诗人。具有强烈的寓言/预言气质。
七 误读
有一回,诗人从西面归来,鞋底沾着黄沙与草茎,胸中充盈着有关月牙泉和胡杨木的记忆,登上了通往温柔乡的阶梯。其时,名妓正在会客之所抚琴弄曲,当即将他引荐给在场的三位尊贵的客人。
居中的一位是身着便服的朝廷大员,待人还算和气,但脸上总有种冷冰冰的、像鱼一样的表情。另外两位都是来自异域的商人——他们的故乡犹如帝国的两个光怪陆离的梦境。二人均出自故国独有的土壤和空气,与各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和植物一起生长,承袭了一些荒谬的风俗,学会了别处没有的智慧和别处没有的愚蠢。在出国经商以前,他们一个是种植金桃的果农,一个是驯养白象的象夫;出于天真的冒险精神或是躲避债务和仇敌的需要,一个骑着神骏的单峰驼,另一个乘坐以木板、椰子壳和鲸油制成的三角帆船,先后来到遥远的异国。在这里,他们得到了财富,但也失去了财富以外的一切。对于他们,帝国是茶叶的深潭、丝绸的海洋和一种魔法般的禁锢力量,一旦进入,便再也不能真正离开。如今,两人都已经很老了,只能等待那最后的渡船,通过泥土之中的黑暗道路,将他们送回久违的家园。
值此良辰美景,可爱的女主人请求李杜为她的客人们即兴吟诗一首。三位佳客立即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期待之情,其中,那位官员的反应尤其热烈,尽管在这间客厅之中,若论感受诗意的能力,他只能位列第六,排在四个活人和一张摆放茶盏的木桌之后。诗人应允,侧身面对别致的,将夜晚框在画境之中的窗棂,闭上双眼,发出梦呓般的声音。他将朗月比作明镜,将浮云比作随一阵轻风在美人颈间飘拂的青丝,表达了一种不具体的、谜样的忧愁。
诗是只能惊鸿一瞥的事物——一首诗就像一只猫,踩着轻盈的韵脚,从地板上一掠而过。然而,诗的后果却是更为长久的东西:遐思、怅惘、一段寂静和几双泫然欲滴的眼睛。
几天之后,李杜在一间廉价酒肆中被人叫醒。来者是官员的仆从,以不容拒绝的态度邀请诗人前往其主人的府邸。两人乘坐马车穿过半个城市,从破败、凌乱、污秽的外城进入豪华、整饬、洁净的内城。之后,由那位精于礼数的仆从领着,李杜迈过了有生以来曾经迈过的最高的门槛,走进了有生以来曾经走进的最大的门户。这座七进宅院的主人早已在第一进院落尽头的门厅中候着他了——与初次见面时不同,这一回,他一身朝服,披挂整齐、威仪堂堂——没有多做解释,只叫下人立刻带诗人沐浴更衣。
待到李杜梳洗完毕,换上一件领口绣有藤蔓花边的绸缎长袍,再回到门前,软轿已经备好。服侍他的下人兴高采烈地催促他,几乎是驱赶着他登上了轿子。这种封闭的、摇篮般的交通工具进一步削弱了本就岌岌可危的现实感。李杜觉得自己陷身于一个无法醒来的梦境,被软绵绵的云团裹挟着飘往另外一重时空。待软轿停落后,撩开轿帘,他的体验马上被再次刷新:迎面而立的是更高的门槛、更大的门户。在他前方,官员已经下了轿,正和守在门前的某人说着什么,看见李杜,便冲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跟上。一行人进了门以后,便沿着在两堵红墙之间延伸的,由雕有各类祥瑞纹样的石板铺砌而成的步道,开始步行。走得久了,脚步在匀速的运动中被忘却,诗人只觉自己如一叶扁舟,正被起起伏伏的浪头推着前进,任由两岸的风景从身畔流过。
眼中所见,只有院落接着院落,屋宇连着屋宇,若是恰好遇上一扇敞开的门,朝内望去,就会发现院落里又围着院落,屋宇后又藏着屋宇。过多的重复使人万分疲惫,诗人怀疑自己根本是在兜圈子。或者,有没有可能,这个蜂巢结构的建筑群纯粹是为了游戏的目的才兴建的?落成当天,它的主人或主人们便从堆积如山的钥匙当中随机抽出一把,然后揣着它,开始漫无目的地转悠,从一个院落转到另外一个院落,寻找自己可以开门进入的房间。有些人很快就找到了,有些人则终其一生也打不开任何一扇门,有些人开了门却发现门后只有一堵坚实的墙……也许,设计者的本意便是建造一座名为“命运”的迷宫。
诗人的想象未能无限度地扩张下去。当忐忑的心情逐渐平复,好奇心便引领着目光,开始四处扫视。厌倦的魔咒被破除了,瓦当、浮雕、凉亭、假山、石桥……许多美妙的碎片便像草丛中的兔子,一个接着一个,从各个角落里蹦出来。这里的每一块空间都像一个巨大、精致的珠宝盒子,其中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在城市的中心,这些盒子堆聚在一起,形成了另外一座城市。它的惊人的美丽,以及它给人造成的完全过剩的印象——这里几乎无人居住——使它像一座宏伟的坟墓,或一座崭新的废墟,似乎在成立之初,它便站在了时间的尽头。
这座城市之中的城市,规模超过了将它封装在里面的大城,就像一个孕育在子宫当中,身材却大过母亲的胎儿。当然,此处的规模指的并非空间的规模,其之所以大,全在于容纳了一种精神上的庞然大物:帝国的灵魂。李杜问自己,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莫非竟是皇帝的居所?他猜对了。
诗歌与权力的遭遇是语言的自我撞击:在那个瞬间,语言形似双头蛇的构造显露无遗。在某种意义上,皇帝与诗人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他们都是被指定的人,是被借用的人,是灌满了语言的皮囊;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发号施令的皇帝便不再是皇帝,不写诗的诗人却仍然是诗人。
皇帝在他的寝宫接见了诗人,他最宠爱的妃子在一旁陪同。由于早已习惯于想象对方,见面之初,他们对彼此的观感与幻觉相差无几,所以才会忽略一些再明显不过的东西:皇帝没有看见诗人的卑怯,诗人没有看见皇帝的衰老。他们被摆在对方建构的神话之中,相互瞻仰了一会儿。接着,皇帝背诵了几首李杜的诗歌,并要求他进行解说。这显然是一次粗暴的入侵——诗人的领土不允许任何既定的解释驻扎其中。但皇帝的金口玉言不容拒绝,李杜只能遵命。过程十分艰难,结果令人沮丧。他看到,那些发光的诗行本来像排列整齐的星辰,悬浮在清澈的空气中,而自己却像一个愚蠢的、试图弹奏波纹的琴师,用笨拙的舌头搅浑了诗意的湖水。最后,亏得那位妃子解开了上谕和诗句绑结的死扣。此前,她一直微笑,未发一言。
“诗人在诗歌之前,解读在诗歌之后……皇上啊,咱们混淆了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倒叫人家为难了。”她说。这时,李杜终于得到机会端详眼前这位迷人的女性。只消一眼,他便理解了皇帝对她的爱,也理解了皇帝对诗歌的爱——她的美丽和智慧都属于灵感的范畴,爱上她和爱上诗是同一回事。换句话说,她是一个被写作和吟唱出来的女人,是一首由眼波和肌肤构成的绝句,她的作者怀着无限温柔的心绪创作了她,却不慎叫一阵恼人的微风将她送进了尘世。
一? 源始
二? 语言
三? 巨人
四? 英雄
五? 预言
六? 桃源
七? 误读
八? 远航
九? 爱欲
十? 信仰
十一? 自由
十二? 流放
十三? 祛魅
十四? 终结
十五? 写在时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