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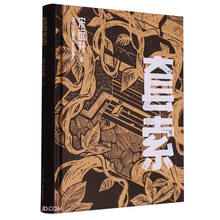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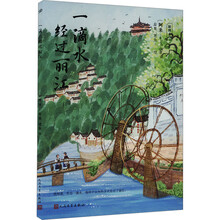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 重庆文学奖得主、实力派作家宋尾构建迷宫般的短篇,谜底就是人心
用十个短篇,勾勒烟火重庆的精气神
如果你说被遮蔽是一件不幸的事,可事实上,大部人在努力地适应这种遮蔽。被生活淹没是一种显然的现实。虚构的作用,无非是把被淹没的人们,湿淋淋地塑造出来。经过围墙时,没人会觉得自己被它的阴影遮蔽。就像那几辆废弃的汽车,没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在熟视无睹的地方,就是故事的空间。
下汉口(节选)
家里最先醒来的人总是婆婆,其次是父亲、母亲,最后是我。
这天也不例外。不过,这次我不是被他们揪着耳朵拉起来的,也不是被他们的吵骂惊醒的。总之,我一醒来就会听到吵闹。可以是为了任何一件事情。婆婆拖板车收完街上的垃圾回来,如果仍母亲躺在床上就会被咒“懒得屙血”;有时是母亲埋怨父亲没有帮她把麻袋搬到板车上。
母亲从棉纺厂下岗后,婆婆开起了旅社,但这个营生显然并不需要两个女人。有天母亲看到电影院的独眼老爹要转让自己的书摊,果断地承接下来。现在,堆在墙角的那八个蛇皮袋里的武侠和言情书,维持着我们这个家。
实际上,吵架有时根本没有原因。他们习惯了,所以我也习惯了。我躺在他们的吼声里继续做梦。可母亲在吵闹中还不忘突然扯掉我的被子,喝令我立即起床。但今天我不是被吵醒的,我觉得是身体里有一根弦把我拨响了。
这次吵架是为了带在路上的几个白水蛋。
母亲煮是煮了,但她煮了三个。被婆婆狠狠地咒骂道,“蠢得冒烟!煮三个,哪个吃,哪个不吃?”矮小的妈妈不大敢跟她对骂。“你们一人一个,我又不吃!”“我吃?你哪次看我吃过你的蛋!”
她们争吵时,父亲耷拉着肩膀,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掰拾他的单波段收音机,迎春牌的。那个东西时好时坏,所以他成天拿把螺丝刀,拆开捣弄半天,有时能行,有时又不行。于是他总这样撬来撬去,一直到收音机的各种零件和螺丝滚得到处都是。最后总是只剩下一个壳壳,和一块主板。这个收音机大概也好不了了。我一边想一边端着搪瓷碗来到后门梯坎上,对着火红的鸡冠花,边撒尿,边刷牙。院子里原来有一只大公鸡,现在它死了,被我们吃进了肚子。还有两只下蛋的母鸡,一只在院子里散步,一只被装进一个布口袋——剩下一个乌突突的脑壳在外面转来转去,今天它将被我们带到汉口去。
那三个白水蛋最终谁也没吃。被包进一个小布袋,放到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那里面鼓鼓囊囊,塞满衣服、毛巾和袜子。“蛋放在那是最安全的。”婆婆忘记了不快,为自己的小聪明乐了起来。她是那种极易满足的女人。
她们执意送我们到长途车站,这似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路过生产街菜市场,母亲去早点摊上买了四个肉包子,我吃了一个,感觉有点腥。我告诉母亲时挨了她一顿好嚼:“哪里腥?你嘴巴腥!肉哪有不腥的!”她将剩余的包子也塞进包裹,拿一张试卷包着。
如果不是凭票进场,她们肯定跟我们到车上直到发动,可是长途车站兴检票了,她们被拦在外面,一脸沮丧。我却顿时轻松了不少,跟着肩挑背驮的父亲跨了进去,一个面无表情的登记员冷冰冰地瞟了一眼车票,扯下票根,像轰鸭子一样把我们吆上了车。
车上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乘客,但整个车厢似乎已经被塞满了。货架上,座位下,驾驶室,走道,甚至引擎盖上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物品。这时我才理解婆婆说的,“东西实在带得太少了!好难得下一趟汉口,该带的都要带上。”可是又如她所说,家里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可带的。除了行李,那只母鸡,她翻遍了整个屋子,终于找到一小袋子炒米,那是前阵子乡下亲戚用一辆二八自行车驮来的;还有就是在菜市场刚买的十五个锅盔。“谁让我们穷呐!不过,”她说,咂了一下干瘪的嘴唇,“你幺大最喜欢锅盔了!蒸肉的时候,垫一个锅盔,不晓得几好吃!”她喜欢什么就说“不晓得几好”!她总是说汉口几好几好,说得好像她去过一样。
这是我头一次出远门,也是我头一次单独跟父亲呆在一起,还要挨得那么近。
不像我们那条街上任何一对父子,他从不问我“你成绩怎么不行啦”、“晚上你想吃点什么”、或是“这个暑假你想去哪”?从不。我相信他连我读几年级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屋里撞见了,总是漠然地擦身而过。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是说,以当时我的年纪很难考虑到这种问题。我刚十岁。还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有多憎恶。只是惧怕,就像鼠与猫的关系,不是迫不得已,我尽量不跟他接触。
他是街上出名的酒鬼,从晚饭开始喝,可以一直喝到凌晨。有时他喝着喝着会突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酒话,问题是,我从来都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他哭哭啼啼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整条街都挪走,叫别人听不到他的嚎啕。可街道是挪不走的。
我母亲就习以为常,“他哭他的,你睡你的,当他不存在。”
可是,他明明存在呀。他不光会哭,还会发酒疯,冲着所有人咆哮,砸碎所有的碗碟,以及一切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尽管我家已没什么可扔的东西了,连大门上也有他踹过的破痕。我最怕他动手,因为挨打的总是母亲。偶尔,那种粗暴也会转移到我身上——有一回,我被他倒挂在床架上,用皮带抽了十几下。但那次他是清醒的,原因在我,我撒了谎被他捉到。
其实白天他并不是这样。他不是暴君,而是一个清秀、寡言的人。往往这时,邻居们蹲在门口笑话他昨夜是不是又发酒疯,别人戏耍时他也跟着笑,像个犯错的孩子。说起来我还从未见过他哈哈大笑。从来没有。
这时他已经病休在家了。婆婆说他之前在县里的第四机械厂烧锅炉,也就是站在锅炉前铲煤的工人,婆婆说他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一,铲不了煤了,就被调到纠察队去了。婆婆说到胃的时候还要拿手比划,“这么长”。我似乎真的看见那遗失的形象,就像一块完整的猪腰子。可是,无论哪份工作我都觉得跟他不符,对不上号。他太清秀了,又太腼腆了,他怎么可能铲煤和抓贼呢?总之,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更符合他。
相比而言,我偏向于白天的他。但总归来说,不管是白天的还是晚上的他,我都尽量避免跟他接触。当然,能够让我们接触的时候并不多。
但这次不可能了,我得紧紧地挨着他,而且还要跟他待上更久,从上午9点半开始,我们像两个陌生人并排坐在从县城驶往汉口的长途班车上。
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大湖
礼拜一闭馆时刻
我们的清晨
那些荒芜的雨滴在夜里明亮极了
两个人住
找狗的人
一个没有准备的地方
下汉口
聋哑人集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