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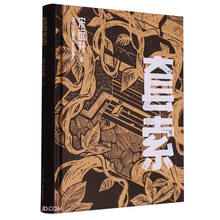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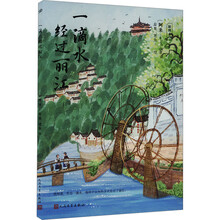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上岭说客
他一辈子几乎只做一件事:晕闻。
晕闻是壮语,意思是劝说别人。晕是劝说,闻是人,那么晕闻的人,就是说客。
樊宝沙是上岭村的说客。他是我堂叔,从我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他走村串户, 去做说客。他凭着一张嘴,或三寸舌头,说服了一个又一个人,解决了一桩又一桩事情。只要他出马,杀人的人能放下刀,盗窃的人会交出赃物,骗子和撒谎的人会吐出真话。
我清楚地记得我五岁那年, 樊宝沙去劝阻韦光益和潘秀香夫妇把女儿送人,那过程和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寒冬腊月的一天, 我还蜷缩在被窝里, 有人抠我的脚心,弄得痒痒的,我不断地蹬腿,脚心还在被人抠。通常爸妈把我弄醒和鼓捣起床,都不是这样的。这人是谁呀?我被迫掀开被子跃起,定睛一看,是堂叔樊宝沙。
堂叔樊宝沙那年大概三十岁,精瘦得像个猴,满脸胡子,手上和腿上的毛都比别人长,更像个猴。他唯一和常人一样的地方,是一张嘴。他的嘴,薄薄的两片唇,干巴巴且紫黑,像是烤煳的红薯被切开。它在夏天和秋天红润一些,像是有油水涂抹,其实没有,是夏天和秋天气候湿润的缘故。到了冬天和春天,气候干燥、阴冷,嘴就会皲裂,像皲裂的手脚一样。在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村到处可见这样的嘴。如果说堂叔樊宝沙的嘴与众不同,就是他太能说了,太会说了。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一套一套的,句句管用,像是从仓廪里输出的粮油,甚至鱼肉,让人不得不服,不可能不受。
堂叔樊宝沙咧着嘴对我笑,说:“想不想吃糖果?”谁不想吃糖?我像看见诱饵的鱼,立马点头。
“快起来,跟我走。”
我穿上我认为最好的衣服,从里屋出去,看见堂叔和我父亲在说事情,听不太清,好像是谁家卖女的事,和我将要得糖果吃没关系。两个大人见我出来,停止说事,把目光投向了我。堂叔上前来,抓住我的手,牵我走。我假装不愿意,或装乖孩子,回头看父亲,征求或请示他同意。父亲没有动作和表情。堂叔见我扭扭捏捏,说:“我跟你爸讲过了,借用你一下。”
我以为堂叔是带我上街,因为街上才有糖果卖。想不到他带我走往的是与街相反的方向,走着走着,进了村里的某家我后来具体地知道是韦光益的家。
这户人家我更小的时候应该来过,有些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分的破陋,房屋的泥墙四处开裂,房梁腐朽,屋盖的瓦片残缺不全。房子里除了锅灶和一张床,一些农具,再也没有有用的东西。与我家相比,那是差得太多了,我家有三张床,有碗柜、缝纫机和收音机,还有一头牛。这家这些都没有,这可能是我后来不再来的原因。我今天跟堂叔来,是因为有糖果吃。可是我不明白,我有糖果吃跟比我家还穷的穷人家有什么关系?我现在看到这家唯一的变化,是多了一张小床,是竹子搭的,歪歪扭扭,快要垮了。
堂叔樊宝沙与韦光益在两张小矮凳上坐着,面对面。说是面对面,韦光益一直低着头,像是愧疚或丢脸的样子。他身着单衣,脏兮兮的,打着补丁,应该四季都穿着这身衣服。他脚穿的是草鞋,鞋绳是橡皮筋,看上去又糙又硬,像是从旧轮胎上剪下来做成的。再放眼看去,房屋里还有人,至少有三个比我大或比我小的孩子,躲在两个倒扣的箩筐后面,抓着箩筐,在看堂叔樊宝沙和韦光益,或是看我。从长相看,都是女孩子。我认得她们中比我大的大姐,她来我家借过米。眨眼间,发现还有人,是刚从屋后进来的,一个裹着头巾的妇女, 我后来知道叫潘秀香,是韦光益的妻子。潘秀香怀里抱着襁褓,襁褓中肯定有婴儿,刚才我分明听见屋后有婴儿的哭声,有女人音在哄,现在看见了人,没有了声音。我发现女人和女孩们都屏息静气,听两个男人的谈话。
我站在堂叔樊宝沙一侧,看见他扫视了一遍房里的三个女孩和潘秀香怀中的襁褓,然后对韦光益说:
“要卖的是哪一个?”
仍低着头的韦光益说:“不是卖,是送。”“送哪个?”
“不太晓得,我舅娘介绍的,是我舅娘那边的人家,今天人家就来了。”
“我的意思是,你四个女孩子,要送哪个给人家?”堂叔樊宝沙说。我从他的话里才知道襁褓里的婴儿也是个女孩。
韦光益这才抬起头,视线移向潘秀香怀里的襁褓,像生怕女婴听见一样,只努了努嘴。
“为什么是她?”
“她刚生,不懂事。”韦光益低声说,“人家好当亲生来养,大了也不会以为不是父母亲生的。”
“这一点你倒是鬼马。”堂叔樊宝沙说,他眼光投向潘秀香,“抱过来,我看看孩子。”
潘秀香抱着襁褓过来,把孩子呈现在堂叔樊宝沙眼前,也显露在了我的眼前。我看见襁褓里的婴儿,小不拉几,面黄肌瘦,像菜地里被水淹的南瓜。
堂叔樊宝沙看了婴儿的样貌,却说:“这孩子天庭饱满,眉清目秀,鼻子高挺,耳垂肥大,是富贵相啊!”
韦光益露出苦笑和冷笑,像是表示不信。潘秀香的眼睛倒是露出了点亮光。
堂叔樊宝沙说:“起名了吗?”
“韦四红。”韦光益说,又摇摇头,“送人后要改的,至少改姓。”
“生辰八字?”
潘秀香边想边报出韦四红出生的年月日时。我只隐约记得是9月1日8点。韦四红大概比我小五岁零两个月。
堂叔樊宝沙用心记下,然后掐指算,嘴里默念着什么,过了很久,才张大嘴巴说:“四红这孩子八字格局,是专旺格。专旺格中属稼穑格,格局中有地支三合、三会,而且有食神泄秀,正印护身,格局清纯高贵,结合相貌、姓名, 是富贵双全的命。”他顿了顿,忽然呼喊:“这孩子不能送人呀!”
韦光益一震,看了韦四红几眼,然后把目光投向了另外的三个女儿。只见三个女儿瑟瑟发抖,紧紧抱成一团,还在发抖。
“其他女儿也不能送,一个都不能送!”堂叔樊宝沙斩钉截铁地说,他站了起来,对除了我以外的人指手画脚,或评头品足,意思是韦光益全家的人, 相生相成,缺一不可,阖家团圆,勠力同心,将来才能发达兴家,福荫后代。他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
潘秀香情不自禁亲了襁褓中的韦四红一口,又亲一口。她另外的女儿们也都放松了许多。
韦光益仍高兴不起来,或者还有烦恼,说:“可现在我们家那么多口人,养不起呢。”
“这你就短视了,井底之蛙,”堂叔樊宝沙说,“穷和困难是暂时的,天无绝人之路,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对未来的生活要有信心。”他这时把我拉过来,推到韦光益前面,“晓得我为什么把他带来吗?我侄仔。”
韦光益看看我,又看看堂叔樊宝沙,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看看,我这侄仔样貌,白白嫩嫩,面若中秋的月,色像春晓的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目若秋波, 南人北相——南人北相贵人命,晓得吧?”堂叔一边摸着我的脸和眼眉一边夸我。
上岭恋人 / 1
上岭侦探 / 19
上岭产婆 / 37
上岭说客 / 49
上岭裁缝 / 65
上岭保姆 / 81
的确良 / 95
桑塔纳 / 149
下水道 / 171
靠名字吃饭的人 / 185
黑夜里的歌王 /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