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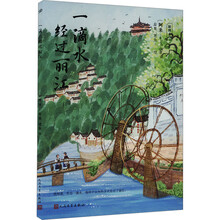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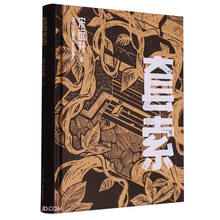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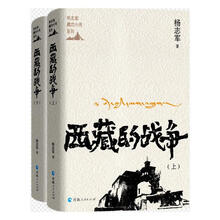
本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一种精神,联大的后人延续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延续百年,长久不衰。时代需要这种精神,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本书是一部长篇纪实体小说,有关西南联大后续的故事。西南联大的历史好比璀灿明珠,但与今天的读者尤其青年读者有一定距离。本书以并行的两条故事线索描写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西南联大后人,使其成为连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书中将当代生活与联一代的历史互为穿插,西南联大历史相关的部份均为纪实,故事本身则以小说模式展开,内容虚实互补,时空交替转换。揭示的是西南联大前辈对后代的影响,后代对联大精神无形的守护与传承。本书强化了纪实体小说这种形式,在借助当代故事科普联大历史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
成都,武侯区。几株高大的老柏树下座落着美国领事馆,门里门外都站着武警,气氛有几分森严。
这里每天有人排着长队等待签证,但赴美国的签证却不大好办。因为,每个人都必须面签,也就是须来与签证官会晤和面谈,而被拒又是经常的事。所以,能否过签,只能凭运气。
一大早,刘开梅和丈夫安志离开酒店,赶往领事馆。
他们要去美国看望女儿、女婿、外孙,花费很多时间准备签证资料,曲折辗转才备齐了各种证件证明,又从所在城市专程坐火车赶到成都,为的就是来与签证官面对面。
“老安你说,我们能不能过?”刘开梅伸出一只胳膊挽住安志,边急步走着边转头问,她的感觉有点如临大敌。
“唔……”安志沉呤一下,没有说什么。
来到老柏树下,他们站进指定位置排队。
据说,如果申请得到签证官同意,他会当面说:“恭喜你。你过了。”反之,资料会被从窗口下轻轻推出,那就表明:“你没过”。
于是“过”与“没过”,成为此时排在队列里的人们内心的焦点,成为他们的宿命,当然,也成为刘开梅心中放不下的焦虑。
两支并行的队伍移动都很慢,每一个人都只得耐着性子。
十一月的朔风掀起安志的领带尖,他穿着深灰色的呢料西服,几分花白的头发整洁地梳往脑后,脸上还能看出青年时代的俊朗,七十岁刚出头的人,神情泰然地站在那里,看去只像六十出头。
“你里面应该加个毛线背心。”刘开梅说着,帮他扣上了西服扣。
她着一身暗红色厚绒秋裙,外罩一件黑色风衣。年纪五十上下,看去身材姣好,蛋形脸上的五官也比较精致。
“你们是学校教师吧?”并排紧挨着的那个队列里有人和安志搭讪。
“我俩都在成州大学工作,我先生是教授。”
安志还没开口,刘开梅抢先回答了人家。对方还想聊点什么,队列里一个穿黄毛衣的女子突然指着左前方说:
“你们看!我猜那几人没过。”
众人看过去,两男一女从出口走来,明显都满脸不悦,其中一个在忿忿不平地说话。队列外不远,有个替他们拿着包,站着等待的人,此时迫不及待地大声问:“怎么样?过了么?”果然,那边答,“没有!”“会议通知都给他了,人家看都不看,推出来了!”
黄毛衣目送那几人走远,转头对身边男人说:“听说有俩夫妇来,男的过了,女的没让过。”男人听了没吭气。黄毛衣摇着男人的胳膊:“哎,咱俩要是都过,那好说;都不过,那也好说。要是一人过了一人没过,那怎么办?”
男人想都不想地立即回答:“那就俩人都不去了嘛!”
“老安,”刘开梅内心忐忑,扯了扯排在她前面的安志的衣袖,安志知道她在想什么,没吭声,安抚地轻拍了那只扯着他衣袖的手。
慢慢地他们排到了进口的门边。
安志前面的几个人被放进去了,他和刘开梅也就自然往里迈步。不料被门里一个胖胖的女警恶声制止,只得退回来仍站在门外。
过了约半分钟,穿警服挂警棍的胖女人放他们进了那扇门,进门后就让站住。胖女人拿过安志的护照,看看上面的相片,然后盯着他厉声问:
“你叫什么名字?”口气像审问。
安志真想一个巴掌打在那副虚张声势的胖脸上,不就是来签个证,至于吗?!但他只能沉住气,凛然提高了音调回答:“安,志!”说到志时声调比说安时还高,还强硬。
胖女人本想威风一番,不料讨了一脸灰。其余警官脸上则露出了可以觉察到的微笑。负责安检的警官十分和颜悦色的接过安志的文件袋,进行了既定程序的检查。
进来以后还是排队。要排到小厅里面那个窗口,才是与签证官“面谈”。每一个申请去美国的人,无论探亲或是旅游,无论公事或是私事,能否成行,那是最后决定的一步。
终于轮到他俩站在窗口面前了。
签证官长着弯曲的综色头发,深凹的蓝眼睛。他问了他们几个问题,然后要求出示各种证件,最后要求出示邀请书,还有邀请人的出生证明。谈话过程中那双蓝眼睛不断注视面前的电脑屏幕。
几分钟后,他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对刘开梅说:
“女士,你过了。”
他留下了刘开梅的护照,把安志的护照从窗下缝隙中推了出来。
几秒钟的感觉意外后,安志明白了眼前的局势。早就听说这签证被拒就被拒,没有任何理由;但其实,总该是有个理由的。今天既是遇上了,问一下又何妨?于是他用英语向玻璃窗内问道:
“签证官先生,能请问一下吗?我,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过?”
听到安志纯正流利的美式英语,再看到他的坦然微笑,棕色头发的态度随和了很多。他用行云流水似的英语回答:“邀请人,只能邀请她的亲生父母。出生证明上写着,生母是她,”他指了指刘开梅,“而生父是另一个人,不是您。所以……”他耸了耸肩,表示抱歉,拿着笔的两手也跟着往外摊了一下。
安志听着“哦”了一声,说:“我明白了。谢谢您。”
他彬彬有礼地向窗内举了举手,然后和刘开梅转身离开窗台。他们侧着身子走过排着的队伍,这时,一个高大的欧州人轻轻拍了拍安志的肩膀,用英语说:
“我在这里排了有四十分钟了,一直在看着窗口。您是这位签证官唯一一个对您微笑的人,也是第一个对您说了这么多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