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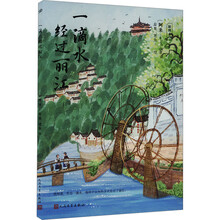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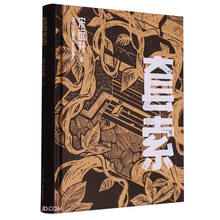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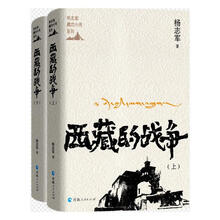
它是2015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绝。
陈彦先生的长篇小说新作《装台》,别开生面,地气盎然,真实可触,引人入胜,叫人为之笑也为之哭,为之思也为之叹,为之摇头也为之伸大拇指。它是2015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绝。
小说写了上百个人物,活灵活现,如闻其声,如见其状,如感其心,为之喜怒哀乐、悲欣交集。百色人生,都是紧接地气,却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知所未知,既扎实,又奇异,既合情理,又绝顶新鲜古怪的当代中国故事。读来令人不忍放下,击掌称快。
——王蒙
陈彦是戏剧家,戏剧家笔下就是戏多。《装台》写了一个陌生行当里的一群人,写得九曲回肠!这部小说难得之处在于“说话”,说的都是明白话、心里话、有劲的话。说出了一个西京古城,也说出了世道人心。
——刘震云
《装台》中曲尽世情悲欢。陈彦写古往今来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从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世界中发现并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物形象,既有人间的热闹,又有广大的冷清。
——阿来
很少有一本书会像《装台》这样,我拿起来,竟心甘情愿地走下去了,它的语调完全是讲述的、口语的,带着明确的地方口音——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是锋利入微,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是老戏骨评说人生的戏,是雅俗不拘、跌宕自喜。在那喧闹的生活里,在那些浑身汗臭的男人和女人身边,和他们一起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竟不想放下不想离开。《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那个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戏与人生、幻觉与实相、心与物、欲望与良知、美貌和白骨、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成功和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此处是盛大人间,有人沉沦,有人修行。
——李敬泽
一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
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发眯瞪的断腿狗,一骨碌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保护伞顺子去了。
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迸碎的陶片,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撸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
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踮在地上,还惶悚得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惯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话了。
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最多也就嘟哝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了。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她才回来第一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
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到床边哄,手里剥了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
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
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留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磨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哟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腕拢到了床上。
虽然才是晚上九点多,顺子就灭了灯。
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又早早没了灯,就有些着急,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顺子骂:“没良心的东西,见不得别人锅里米汤起皮,难道也见不得我米汤锅里沁点油花花。”把蔡素芬惹笑了,扑哧扑哧的,如放了气一般的绵软无力。
正在他们享乐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菊花已经下楼来了,她先是上了趟厕所,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故意把水开得很大,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地响,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顺子和蔡素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静静等待着。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间,又撂出一句狠话来,像是一支毒箭,直接穿过窗户,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
“尾巴一揭,只要是母的,都能领上床,哼,贱种!骚货!”
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猛地翻起来,就要发飙。
蔡素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说:“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是咋样把你拉扯大的,你就敢说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今天无论如何,是得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可蔡素芬咋都没让他下床。蔡素芬就那样死死把他腰搂着,直到他唉声叹气的,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
可这晚上,顺子也再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
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早早安寝了。
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素芬突然说浑身痒痒,问:“是不是家里有虱子?”
顺子迷迷糊糊地说:“瞎说,早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了,先前有。”
“哎哎哎,都爬到我身上了,还说没有。”
顺子就开了灯,一看,是蚂蚁,还不是一个两个,越找越多,个头都一般大小,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这些家伙,单个行走,几乎不容易发现,一旦集体行动起来,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
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说:“是蚂蚁搬家。咱这村子,蚂蚁多,不稀奇,小时我们经常看见蚂蚁搬家哩。”他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就打开门一看,果然,月光下,一支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经过七弯八折,最后消失在了西墙脚的一个窄洞里。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而跑进卧房的这些,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素芬问咋办,顺子说:“它搬它的家,咱睡咱的觉,估计天亮就搬完了。”顺子说着,把床上的被子拿起来抖了抖,素芬就用脚,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顺子急忙制止说:“别踩!”他用扫帚把那些蚂蚁都扫进灰斗里,然后拿到蚂蚁队伍前,轻轻倒了进去。
素芬就笑了,说:“你是吃斋念佛的呀?”
“唉!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