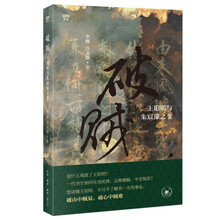一泓碧水,一座铺满青苔的石桥,每日晨起萦绕山石回廊苍凉的三弦声声将这座回龙街小院的身世尽显神秘而诡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暮秋。斜阳探入小院西窗,一位民国富商微睁双眸。梧桐疏影将他的苍白面容染上阴惨的暗色。他翻了翻身,惨白的手指指向镶着金边的穿衣大橱。倏忽之间,他的手垂下了。一个长相清俊的年轻女子满面惊骇,一步跨前,跪在床前。
富商名叫黄鹤,原籍皖省巢湖。自保定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十年打拼,成为皖系军阀一举足重轻的实力派。一次皖系军阀混战中,他不幸落败了。脑袋瓜灵活的他,弃武经商。他从小对丝绸业谙熟,先盛泽,后常熟,最终在苏城落地生根了。
尽管胸中文墨不多,他却沉醉于琴棋书画,与一帮苏地文人琴师往来频密。在市中心一风雅小河畔,一座溢着徽派气韵,东院西园的宅邸跃然于世。不久一位容貌清雅的绣娘入住了。他的原配则无奈地在巢湖之滨过着青灯黄卷,富足而又愁闷的日子。他曾尝试将她接到苏城。“有我无二。”粗通文墨的原配夫人的愤怒回复震撼了这位皖商。在巢湖农舍长大的幼子居然长得和后妈绣娘脸形相似得惊人。“天意,此乃天意。”这位风雅儒商得意地藏着一个惊天秘密。其实,这位幼子即是他与绣娘暗度陈仓的结晶。一个月黑风高夜,当黄师长抱着一个长相秀逸的婴儿闯进巢湖农舍时,他“砰”地跪倒在一个目光慈蔼,身形瘦削的农妇面前,泣不成声:“孩子的爹为我而亡,他的唯一血脉委托我养育,拜托了。”言罢,他掏出了一张血书,一个金镯。农妇的眼眸跃出了泪花。“孩子就叫一武,长大后,为国雪恨,为家报仇。”农妇略通文墨,她含泪点了点头。数载后,这位武场落败的将军在姑苏安了一个小家。一位清丽的绣娘,孩子的生母,在唢呐的吹奏声中与这位双手能打枪的前师长拜了天地。那位救他一命的前参谋长至死都不知道他的姨太太,那位貌似高雅,行止端庄的绣娘曾创造出军营深处这一荒唐故事。“我是姑苏的准女婿。”一次喝高了,黄师长斜瞄着他的挚友,晃了晃手中的酒杯,醉意朦胧地说。参谋长大吃一惊,只见他涨红面孔高声喝道,胡说。黄师长眼里掠过一丝惊恐,酒醒了。他冷笑起来,大手一挥“戏言,戏言”。次日,一场血战中,参谋长身亡了,离奇的是,子弹是从身后射向他的。黄师长假意泪流成河,伏在好兄弟的身躯上颤抖着:参谋长仇恨的双眸圆睁着。巢湖边上小小少年在农妇的精心呵护下快乐成长。只不过,这位师长的宁静生活被一位仗义的好兄弟的一次造访打破了。一个漆黑的姑苏夏夜,一个人影窜入黄师长水秀花明的宅邸。黄师长打开宅门,一见来人杀气腾腾的面容,惊呆了。回龙桥畔。黑影宛若一道利剑,又好似一团烈火,将黄师长宁和的生活撕得粉碎。来人正是黄师长密令枪杀参谋长的凶手。当这位枪法一流,年方二十名叫谢鹰的狙击手从背后向那位黄师长昔日的好兄弟扣响板机时,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五百大洋的叮当声响在他的脑际腾起狞笑。五载后,他亦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一番,只落得两手空空,更使他度日如年的是债台高筑。一个邂近,让他知晓昔日参谋长的姨太太竟然变成了黄师长豪宅的女主人。撕破黑幕,狠狠敲他一笔,一个罪恶的念头诞生了。他抬头大笑三声,从柜子里抽出一个信封,将一颗子弹放入其中,心里泛起了喜滋滋的浪花。咚咚咚……如雨的叩门声惊飞了芭蕉树上熟睡的黄雀,黑漆大门紧闭着,只有一星灯火悄然亮起。头戴巴拿马礼帽的谢鹰飞起一脚,把门踹开道裂缝。门灯下,探出一个怒目灼灼的中年人的面庞。“放肆。”一声高喝从高墙内威严传出。又是一脚,这力拔千钧的一脚猛踢将厚实的大门哗啦啦踢倒了。月光下,壮小伙迅速拔出腰间的盒子枪。只见立于门内身躯高大的黄师长眼里闪现一道狡黠的光焰。他猛地一拱手,仰头朗笑起来:巢湖水冲垮了龙王庙,好兄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他猛跨一步,牵起来客之手,小谢,有啥难处,尽管言明,我黄某当尽力相助。黄师长与他有知遇之恩,又是巢湖边上共饮高梁酒的好兄弟。想到自己的失态,谢鹰额上沁出了汗珠。入厅堂,穿月廊,竹影深处,汩汩河水绕着一幢清雅小楼,黄师长的卧室到了。“鹤哥,”一声清脆的呼唤后,随着踏踏踏一阵疾徐脚步声,绣花门帘被一双纤手快速掀开,一张杏眼怒睁的少妇脸庞映入谢鹰惊悚的双目。“我倒要看看,今朝闯进伲屋里的是一只秃鹰,还是一只落汤鸡?”少妇紧了紧高领绿色旗袍,双手叉腰,厉声地说。谢鹰并不答话,只见他从军装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大太太的诉状,他冷笑一声,随即啪地将一颗血染的子弹猛地掷到方桌上。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