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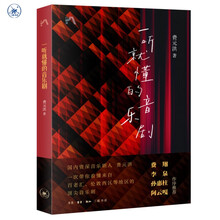









红白蓝三色斜条纹连续排列,在底边镶出一条充满动势的狭窄跑道——我从小钟爱的航空信封。当我在邮局里蘸了胶水往鼓鼓囊囊的航空信封上贴邮票,总能感受到工作人员异样的目光。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而且这么长?作为通信原教旨主义者,毕业之后,我给你寄过十封信。除了第一封,没收到过回信。
你没来过沈阳。你是地理盲,甚至不知道沈阳是城市还是一个省。我在信里长篇大论为你讲述沈阳新貌。曾经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城市(什么叫重工业可能你也不太明白),如今走在慢慢衰败的下坡路上,像无力回天的老人。但和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一个无法概括的城市。它并非仅仅出产小品演员,以打架斗殴为荣的小混混和文艺作品里破碎的铁西区下岗家庭。这里的人无论出门办什么事,哪怕到商场买个电饭锅,都会先在脑子里盘算怎么能托到熟人,然后打上数个电话(人情社会特征)。谁家闺女找了男朋友,大妈们聚在一起饶舌,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多高的个儿啊”(农业社会特征)。在新闻里看到其他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上班族疲于奔命,沈阳人会庆幸地感叹一声“咱沈阳真是风水宝地啊”(老龄社会特征)。如果你捧起一本闲书,既非教材,也非成功学宝典,旁人一定会轻蔑地说“看这有啥用啊”。
但同时,你也总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情。一个游客,想拍摄街上的陌生人。换了其他地方,被摄者肯定一脸反感。但沈阳人不会,不仅不反感,还热情地一边聊天一边按你的要求摆出各种造型。你到朋友家做客。经济条件再差,他也必倾力为你操办一桌像样的酒菜。而且东北的语言是多么丰富啊。这里不盛产作家和演员是不可思议的。对沈阳,我说不上爱或是不爱,对地域的感情是不能被这样简化的。
我每天骑车上下班。七点半出门,五点半到家。早晚各半小时混迹于车流,经过同样的十字路口,看同样的交通灯,成了真正的成年人。考虑很远的未来,做别人让你做的事,关心月底那笔工资。
每天回到家我没有其他事情,就大量地看电影。每周十部以上。我按法国《电影手册》每年十佳影片的顺序一部部看过去。然后像山鲁佐德一样把喜欢的电影故事转换成自己的语言讲给你听。我没有你的照片,你容貌的清晰度在头脑中迅速衰减,变得抽象。看到这个电影的演员神态像你,看到那个电影的演员侧面像你,还有某个人穿衣服的风格像你,把几位相加除以三就正好是你。我买了厚厚一本《Photoshop从入门到精通》,学习图像处理技术。把从网上搜索到的元素重新排列组合,裁剪、拼接,再细致地修图,合成想象中你的样子。当然,更好的办法是自己画。于是我在休息日的下午开始去小区对面的一间画室学习素描,画几何体,画石膏像,混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中间。希望有一天能画出你。我画下居住的楼房,附近的菜场,卖玉米的卡车,烤地瓜的老头,把它们夹在信里寄给你,不管画得有多糟。你看了当然觉得可笑,因为你从小学画。你给我看过几张以前作品的照片。你说本来想考美院的,但父亲坚持不准把画画当职业,说不稳定,找不到工作。
在信里我不太讲研究所的事,怕你不感兴趣。老实说,那里的气氛让我压抑。面对一群陌生人,我总是手足无措(我还没学会和比我大十岁,二十岁,三十岁的人平等交谈)。这主要是自身的问题,我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了。我所在的光电信息研究室共有三十多位同事。室主任沉默寡言,头发像鲁迅一样短而硬,左侧腮帮子有个小鼓包,使人感觉他的嘴巴里永远有颗青橄榄顶在那儿。他得过全国青年科技创新杰出奖,一看就特别聪明。他知道我是靠领导关系进来的。第一次见面,很和气地说,欢迎你加入,你新来,就先去做做检测吧。我心里清楚,自己什么也不会,对工作既没兴趣更没热情,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无知像南郭先生一样暴露出来。所以领导越是和颜悦色,我越是对他充满了畏惧。
一屋子全是硕士、博士、研究员,但和你想象中的科技精英不一样。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写程序。同事卢姐一路嚷着从外面进来,哎呀妈呀,可捞出来了。坐我前面的王老师笑着问,卢姐,捞啥去了?捞人还是捞螃蟹啊?主任说,瞅你这一惊一乍的。卢姐向王老师挥舞着手表,这个呗,上厕所掉马桶里了。王老师凑过去问,啥牌的?卢姐把手表往他眼前一送,你瞅,去年德国开会买的。王老师扇着鼻子赶忙闪开,啥味儿啊。你慢点,别哩哩啦啦迸我一身。卢姐嚷道,躲啥啊,哪有味啊,洗得老干净了。她揪起袖子擦了擦表盖说,水管子上这顿冲啊,你瞅人家这瑞士表,真防水。主任也笑着打趣,陕西出了个表哥,咱这儿有表姐。一直埋头敲键盘的刘哥补了一刀,表姐还是彪姐?大家都笑。卢姐也跟着发出智商很低的那种哈哈大笑。
我给你寄信,留的是研究所地址。所以在单位里,每天都盼着你的回信。在唯一的一封回信里你说,一进出版公司就接项目,独立工作了。这就是学文科的好处。你对自己做了很好的人生规划。那封信我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没发现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句子或词汇,也完全不涉及任何私生活。你说你很忙,无法经常写信。读完我就知道毕业前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对你来说,连梦都不能算,也许只是一个错误,或是冲动之下对一个仰慕者的怜悯。
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样问其实是想自欺欺人,因为在那个年龄,还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平庸。
但每天下班路过收发室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进去查一下。管收发室的老头儿金宝贵凶得像头藏獒,他那张黑脸跟泰森的经纪人吸血鬼唐金一模一样“瞅你一天到晚五迷三道的,喝假酒了还是被人下药了”,“天天来瞎翻,这年头谁还写信啊”。我只当没听见,必须确认确实没有你的信,才带着沮丧骑车回家。
寄出第十封信后,我很清楚你不可能回信了。我知道,该停止了。如果继续写下去,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某种骚扰。我不想做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
也尝试过给你打电话。先在纸上列出想说的内容。尽量简短,不能太啰嗦,不能浪费你的时间。信里写过的就不要重复。以提问为主,尽量听你说。工作情况怎么样?不好,这太泛泛。你肯定回答,还行。问题要具体一些。现在在翻译什么书?如果你说出一个我不知道的外国作家,话头不是又断了吗?也不好。问点生活方面的吧。住在什么地方?我对北京不熟,也不是好话题。还是聊聊大学同学的现状吧。刘旭、张晓川、熊晓清都在北京工作,他们怎么样了?也许可以从这里展开。
我又盘算什么时间打比较合适。上班时间肯定不行。午休你可能跟同事一起吃饭聊天,也不方便。下班后呢,八点之前恐怕不合适。北京堵车厉害,你在路上的时间短不了,而且地铁里嘈杂,根本听不清楚。到家先吃饭,吃完少说也得八点了。八点以后打吧,也许九点比较从容一点。我定了九点。我看着表,等着那一刻。不行,不能正好九点,太刻意,再过两分钟吧。于是,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拨你的号码。响了好久,没人接。我提起来的那口气一下子泄了。过了几分钟,你打回来了。你说,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你的口气就跟研究所里人事科阿姨的口气差不多。我说,是啊。你说,有什么事吗?我说,也没什么。很长时间没见了,就是问问你现在怎么样。你说,挺好的。我说,跟熊晓清他们聚过吗?他们怎么样?你说,还没有,现在比较忙,没抽出时间。我说,还挺想念他们的。你说,等国庆节看能不能约他们吃个饭吧。我问你现在工作累不累。你说还好。我说,注意休息,劳逸结合。你说嗯,我会注意。我说,没别的事了,那就先这样吧。你说好。“好”字还没听完整,你的电话已经挂断了。速度快得让我猝不及防,好像一辆高速大货车“嗖”地一声擦着鼻子尖开过去。这个电话,让我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自己。是的,我没有任何一点值得你爱。木讷,无聊,胸无大志,毫无幽默感,要什么没什么。连如何跟一个自己喜欢的异性沟通都不会。同时,受到的冷遇所带来的屈辱感,使我对自己的鄙视加倍了。如果我是你,也会对电话那头的那个人感到厌烦。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只有残存的一点点自尊心仍在和自卑感负隅顽抗,勉强支撑着日常生活。我甚至对人类发明了打电话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气。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
我们断绝了所有的联系。
二○一一
二○一二
二○一三
二○一四
二○一五
二○一六
二○一七
二○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