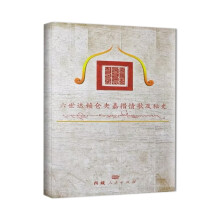爱情诗
今年六月初六,一早起床,太阳很好,是一片耀眼的灿烂。我们这里的坊间兴六月六晒“龙袍”(其实是日常穿戴的衣帽而已)。我在晒自己“龙袍”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存放于乡间老宅阁楼的那一捆书。我已经三十多年没读书了,它们寂寞地待在黑暗的阁楼上三十多年,应该落满了灰尘。
——题记
我读初中时,有一次学校图书馆搬迁,我块头大,力气足,老师就叫我帮忙从一个屋子往另一个屋子搬运图书。我本来不想偷那本书,要怪那个脑袋尖尖、个子矮矮的图书管理员老头,他帮我码了没过脑袋的一摞书,我走路时眼睛都看不清前方。我走到一个花坛边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我打了个趔趄,堆在最上方的一本书犹豫了一下,滑进了花坛月季丛中。我没有第三只手去捡起那本书,我本来想回来的时候再从月季花丛中捡起那本书交给管理员。可是,我当时不知去忙哪件事,忘记了花坛里的书。第二天想起来后,我又担心唠唠叨叨的图书管理员老头会怀疑我故意为之。放学后,我悄悄地溜到花坛边,把它放在了自己的书包里,占为己有。
从此我拥有了一本《普希金爱情诗选》。
我一直认为,我的诗歌启蒙老师是那个叫普希金的情种和疯子,他见到漂亮女人就写诗、赠诗,他写的《给娜塔利亚》《致克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哥萨克》……每一首诗都让我读得泪流满面。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步履沉重、满腹心事地徜徉在学校通往村子的濑水河滩大堤上,我抓着自己的头发在濑水滩涂天空自由飞翔,我不知道自己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我只知道,这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濑水河上古老的石拱桥,濑水滩涂两岸的杉木林,天空中飘浮的白云,校园里高耸的蓄水白塔,阿爹手中牵着的水牛,甚至穿梭在村野之间的三婶母家那条调皮的黄狗,我都认真地给它们写过诗,激情飞扬地赞美过它们。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和我分享激情,分享快乐,我曾经将诗稿投寄给南京一家叫《青春》的杂志社,石沉大海后,我再也没有将诗稿投寄给任何一家杂志社。因此,我们学校的师生,我们村上的社员,他们都认为我热爱劳动,尊敬长辈,不偷不抢,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孩子,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他们身边有一个天才少年诗人。
只有三婶母家的那条黄狗例外。有一回,我在濑水滩涂割青草的时候,看见它在河边溜达,我把它哄到一片荒地上之后,从裤兜里掏出新写的诗,专门为它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那次,我读得泪水滂沱,它听得摇头摆尾,甚至眯着眼睛,用鼻尖来回磨蹭我的膝盖,喉咙发着“呜呜”的声音,像是表达共鸣,又像是催我早点回家。后来,三婶母家的黄狗见到我总是扭头便跑,怎么哄也不回头。
读初三时,我们班换了一位姓杨的年轻英语老师,她披垂着大卷波浪发,看学生的两眼波光潋滟,长相特像电影《白莲花》中的女主角吴海燕。她是全校少数几个化着淡妆,敢穿紧身衣,敢袒露胳膊和大腿的女教师。那个年龄,那种时代,我还不懂得性感,但已经知道见了漂亮女人心痒。我的长辈们曾十分严肃地教导过我,见到漂亮女人就心痒的男人不是正派男人,换句话说是下流胚子。我们家族中从未出过下流胚子,所以,我努力想克制自己的心莫痒。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只要杨老师一走进教室,我就会情不自禁心痒。我对自己很失望,莫非我生下来就是下流胚子?
我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一首接着一首地给杨老师写诗,从她的眼角眉目写到举手投足,从一笑一颦写到星星月亮……那段日子,我的想象力疯狂滋长,它奔放、热烈,色彩炫丽。我发现自己比天才普希金更有才华,我的灵感像村子后面的濑江水,遭遇丰沛的黄梅雨,泛滥了,一浪高过一浪,汹涌不息,绵延不断。有时灵感突然来袭时,半夜我都会溜出宿舍,匆匆地跑到学校最偏的厕所,在那盏老祖父眼睛一样浑浊无力的灯光下,贴着群蝇飞舞的厕所墙面写着,或者蒙在脚臭味浓烈的被窝里,打开手电筒写……
P2-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