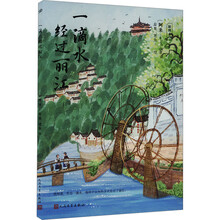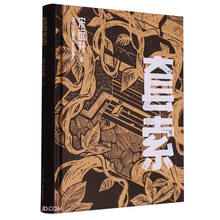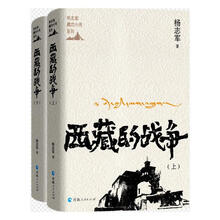千年银杏
银杏树下,横一块青石板,大约两米长,尺把厚,知妹坐在青石板上,很孤单。
知妹什么事也不做,每天坐这里,默默地、安静地看着世界,然后,起身回屋。人们十分惊讶,知妹很准时就来到银杏树下,早上,七点来,下午,五点半走。
很有规律。
银杏树很古老了,据说已上千年,这种具有活化石之称的老树,有三十多米高,灰褐色树身,裂纹苍老,树叶却依然青翠,远远看,如一柄巨大的绿伞。
人们不明白的是,知妹为何每天坐在银杏树下,是它的凉快?还是它的翠绿?抑或是,它能够勾起知妹的回忆?
回村里的第二天,知妹就出现在银杏树下,选择了这个翠绿的地盘,似乎作为栖息之地。知妹爷娘呢,也不再劝,劝过的,劝不听。再说,知妹也没有惹什么麻烦,或哭闹,或寻死路,或拿刀子杀人,或脱衣剐裤,这些可怕的迹象,一点也没有,她是属于那种真正安静了的人,寂寞地坐在银杏树下。
所以,爷娘也随她去,很无奈。
第一天,知妹出现在银杏树下时,穿着淡蓝色工装,帽子也是淡蓝色的,很干净,也很整洁。鞋子呢,是翻毛皮鞋,一看,都是厂里发的。人们暗暗惊疑,大概,知妹还以为是在上班吧?或是,怀念上班的日子?知妹静静地坐在银杏树下,好像坐在宿舍里,随时准备上班,只等电铃嘀嘀一响,就要打飞脚朝车间跑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每过七天,知妹就换掉那身淡蓝色工装,悄然地穿起牛仔裤,红花上衣,脚下是黑色高跟皮鞋。那一天,知妹就像个闲散的女子了。那么,是不是她晓得今天是休息日呢?就换掉千孔一面的工装,穿一套有个性的衣裤了呢? 似乎,也成了一个规律。 知妹戴淡蓝色帽子时,就看不出她的乖态了,好像那些乖态被帽子遮掩了,况且,帽舌又长又宽,跟别的妹子没有太多的区别,一旦取下来,黑色的头发就蓬松了,就把脸庞衬托起来了。知妹的脸很秀气,眼珠子大,下巴有点尖,是圆圆的尖,尖得很好看。加之,衣裤也换了,一身的韵味就显露了出来,坐在青翠的银杏树下,红花上衣,就像突然爆出的一朵硕大的映山红。
知妹不吵,也不闹,好像这辈子没有吵闹过,回到屋里,也是默然的,吃饭,睡觉,洗澡,而且天天洗(有这个必要么),好像要把浑身的机器味通通洗掉,总之,就像一座活动的雕像,很安静。跟白天稍许不同的是,躺在床上的知妹,会从枕下摸出红色的手机,轻轻一揿,音乐就响起来了,是陈琳的,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每晚上,知妹都要听一遍,只听这首歌,听罢,把手机摆在旁边,似乎在等谁的电话。
听她爷娘说,其实,手机从来没有交过费,只充电,让她听听音乐,满足她一下而已。知妹似乎并不在乎,仍然像宝贝一样守着。
当然,知妹也不是一味不语,偶尔,竟然小声说,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种声音,有时含有惊喜跟快乐,有时也包含痛苦跟忧郁。眼神呢,也倏地亮堂起来,不一会儿,火花就熄灭了。
然后,又沉入默然。
人们不明白,她究竟想起了什么,也问过她的,知妹知妹,你到底想起了什么?
似乎没有听见别人的问话,知妹不吱声,也不瞄人,目光沉静地望着远方的大山,一动不动,很固执。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那么,是不是想起了杨家后生呢?是的是的,肯定是的。
知妹的那个对象,村人都见过的,来过好几回,后生长得蛮不错,结实,高高的,穿着银灰色夹克,蓝色牛仔裤,头发梳得丝丝绺绺的,也很懂礼性,见人就笑,就喊,就说着南边那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很拗口。当然,村人是不会计较的,凡是出去的人,一年半载回来,哪个不是说这种拗口的话呢?知妹也说,只是说得很准确,南边的口音几乎没有,是纯粹的普通话。
村人都晓得,后生叫杨志纯,杨家坳上的,跟知妹在一个厂子。
当时,村人就对知妹爷娘说,知妹以后会离开你们的。知妹爷娘猛摇脑壳,不可能么,杨家坳上又不远,才八里路,这算什么离开呢?想看看她了,不就是几脚路么?村人又说,你们以为这些后生妹子还会回来么?还会像我们蠢里蠢气蹲在深山么?知妹爷娘就怀疑地问知妹,知妹说得很肯定,说她不会回来了。
第一次来时,杨家后生带来好多的礼物,肉呀、鱼呀、鸡呀、鸭呀、糍粑呀,当然,还有钱呀,还给知妹爷娘买衣服,给两个弟弟买鞋子。那天,知妹屋里就像过年,其实离过年还早,屋里就热闹起来了。准新郎官来了,看热闹的人去了一层,又来一层,潮涨潮落样的。杨家后生也不怠慢村人,是细把戏的,就笑笑地散糖粒子;是大人的,就客气地张烟。脸上始终是笑,没有一点不耐烦。
再说,杨家后生也不像其他后生,回来就好像是老虎归山,血汗钱往自个爷娘面前一板,大袋子朝桌上一摆,就卵事不探了,似乎要把一年紧张的神经彻底放松,打牌、喝酒,昏天黑地,个个像贪婪的赌棍,醉生梦死的酒鬼,跟自个爷娘都没有几句话说了,过完年,疲惫的眼珠一抹,就匆忙上路,把家乡甩在了屁股后面。
杨家后生不是这样的,喊打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