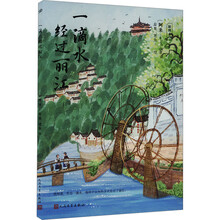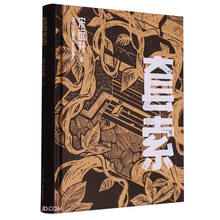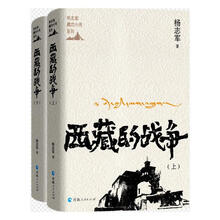这么说吧,那是八月初的一个下午,令人头晕目眩的炙热还在兴头。要在乡下,阳光一定正照着满是收获的土地,蝈蝈在荆棘丛里呜叫,黄色的柴胡花和紫色的风毛菊成片盛开。而我,却在城市的一家咖啡馆和米罗约会。
咖啡馆里,客人不多,多少显得有点冷清。不过,那些独自品着咖啡,或正和同伴聊天的客人们,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轻松自如、从容洒脱,仿佛内心里没有一点尘埃。在“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低沉、舒缓的背景音乐声中,我踯蹰前行,我慢慢打开糖罐,我发现里面只剩下一小勺糖了。可我的托盘里,却摆着两杯咖啡。此时,米罗正双手相叠,斜倚在椅子上。他那两截儿又白又瘦的小腿露在外面,一只脚在桌下不停地踮着,样子既冷峻又自信。究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年轻人掩饰不住的芳华与青春罢了。
我把罐里的糖全都倒进一只杯里后,来到米罗对面坐下。我看似平静地向他解释为什么没有替他拿加冰的可乐或冰镇啤酒。他有两顿饭没有下肚了,说不定是三顿。当然空腹喝咖啡也不好,所以我帮他取了蛋挞和蛋糕。我把有糖的那杯咖啡放到他面前,看着他,希望他坐正了和我说话。
这是我和米罗的第一次约会,正式约会。我们还没开聊,气氛就已严肃。米罗不看我,喝咖啡时也不抬头(我宁愿相信他是自觉理亏),但很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不想再接受别人指手画脚。可我不是别人。我是他父亲。再过一个月,米罗就要离开我,离开他妈妈,像首次离巢远飞的雏燕去往南方了,可他浑身上下的稚气还未褪尽,更要命的是,就在一天前,一个与他要好的姑娘跳楼了,米罗为此抓起刀冲向他妈,尽管母子情深,没有酿成大祸,可毕竟性质恶劣,不能不叫人深思啊。
我试着说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话,算作开场白。我尽量做到语气温和、动作平缓。米罗却似乎并不买账。他神情专注,只是盯着桌上的咖啡看,一直看,一直看,仿佛那杯既苦又甜的咖啡就是他来这一趟的全部目的。这让我们陷入尴尬。我只好也去看他,看他细长的手指,红润却扁平的指甲,右手中指那个泛白的硬茧,以及指关节处那些柔软稀疏的毛。臭小子!手都长毛了!我想告诉他,我不是法官,也不想做法官,我是他的爸爸。但在他看来,这就是法庭,就是审问,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问题要他来回答。是啊,在没有看到他之前,我确实这么想,我甚至还想过开口前要先抽他一巴掌。可是当他,我的儿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那些本来要说的话,就一句也说不出了,更别说再动手打他。
“那姑娘……我是想说,彭波她……,”我最终得和米罗开口说话。我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不会真像大家传的那样吧?其实我想跟米罗说的是,在那几秒钟里,那个叫彭波的姑娘,在空中快速坠落,风在她耳边呼啸,楼房像中了魔,变成一根根直线向上猛蹿,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她搞不清自己是在坠落,还是在上升。那时,她就没想过自己赶紧长出一对翅膀来?毕竟是十八层楼啊,她那么年轻、漂亮,情窦初开。她又不是一袋垃圾。
米罗揉揉眼,但不是哭。我知道他还在心痛,那姑娘是他的至爱,说不定是初恋。初尝爱情的年轻人容易轻狂,难以把持自己,尤其他还是我米海西的儿子。他不接我的话,然后像解说员一样按部就班地对我说,那姑娘跳得很好,很彻底,甚至是完美;说那姑娘至少解放了,再不用“亚历山大”了,也不必再用空洞的笑来掩盖自己的空虚了;一切都云消雾散,归于了真实。他在拿那个姑娘向我挑战,在向我示威。我心里这么想。
可是,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一个叫彭波的女孩跳楼自杀了,无论米罗怎样想她,她都不会再对他笑,他也再听不到她的声音,得不到她的回答了;真实就是,那个姑娘太自私,根本不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自以为结束自己就结束了一切;真实就是她让米罗抓狂、发疯,抓起刀仇人似地冲向自己的妈妈。真不错啊!我的米罗居然这么有出息,他居然用刀比着自己的妈妈。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