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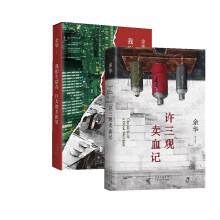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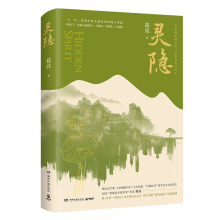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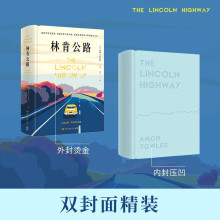

本书为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集,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车马右的耒水地区生活,将善良与邪恶等因素交织起来,以普通人的视角来构建整个故事。本书比较生活化,所描写的也都是人们平常生活当中的琐碎往事,人们可以把这本书当成过去的回忆录。
《蜉蝣》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耒水地区生活为背景,以主人公马车右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叙述了当地人形形色色的生活样貌,以类似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来展示、讴歌中国那个大发展的年代。小说讲述了一批普通人的人生命运。他们或代表善良或代表丑恶,或是可僧的或是可爱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用各自的人生告诉我们:善良和正直永远是生命的主旋律,朴实和真实是生命的永恒追求。
一
上苍是公平的,凭天地之伟力,它给了每一个村庄一件神物或法器,譬如石头村的白头狮、大河滩的百米喷泉、五里牌的四眼井、六甲村的葫芦塔和廖王坪的铁牛(陨石)。马村的神物就是那棵守山树。
守山树下曾经有过许多的马,因而方圆八百步得名“马村”。这棵千年古樟,有猛枝九根,虬曲苍劲,盘亘而上,犹如九龙飞天。其中有一巨枝横卧,枝腋叶梢触及大地,像大锅的勺柄一直伸至马村村口,形似一条神奇的登天小道,曲幽中送你到达古樟之上、云端之间。到了元宵节,这里便成了马村最理想最浪漫的观赏胜地。全马村的乡亲们都雀跃鼎沸在这棵千年古樟的巨臂上,为自家龙灯队欢呼。
马车右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般的樟树巨枝,到达了树的主杆分杈口——一个足有半张乒乓球台大小的、如同巨型鸟巢的树脖窝。窝槽里铺满了经年沉积的腐殖、百年前的鸟粪以及叠生千年的苔藓。他躺在那儿,双手抱头,再一次想起六爷骂他父亲的那句话:“没用的东西!”这话不痛不痒却挖心,使得他牙齿咬得咯咯叫。他并不知道,在距此十五年后的同一个无助无奈的赎罪日里,他会在那魔鬼与天使对决、死亡与重生较量的黑陪的深井中再次想起。
许久前,那时的马村还处在一个蒿草峙立、鼠路飘飞的茅草垄中,风吹草动中现出来的土屋、草棚,宛若一堆腐朽的蜂箱。有民谚道,马村有三怪:十八个蚊子一盘菜,短裤穿在长裤外,妇人洗澡在门外。有人那天看见那个外号叫“三腿驴”的瘦高驼背男人在马厩里撒尿时,面对铁青马吊在肚皮下的玩意整整发呆了半天。其状甚哀。
后继无人,拜堂冷清,是要被同宗同源的其他宗支欺负的。所以.从这个男人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多娶老婆多产子,就成了“家策”、成了“十九担”旁系这一支奋斗的目标。然事与愿违,三代单传,到了这辈上,竞然大有接不上后的架势了——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老光棍。
从马村的后山,过石桥,顺着贞德牌坊下的官道一直走,在一片稻田尽头的枫杨树下,是邻村老湾。老湾古时多出烈女,那石头牌坊就是大明宣德皇帝旌表李氏家族当年在朝廷征伐蒙古时为那些死亡将士的遗孀所立。但这种贞德并未得到传承。老湾有个叫“五嫁娘”的女子。女子十六岁那年正式嫁人,男人是外村的一个老实农民。这段婚姻极短,不出仨月,男人就得病死了。回到娘家还没足月,媒婆又上门说亲了。媒婆说这回得找个阳火重邪火旺的,这样才镇得住该女子。于是乎老媒婆找了个腰间插着两板肉斧游走在耒水上下游,大坳、官洲、大河滩三个墟场逢集卖肉的屠夫。屠夫姓郑,长得高大威猛,一身横肉。那时卖肉是个俏行当,逢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几乎天天开墟,吃口稳当饭是没问题的。目时下又正流行着“四个轮子一把刀”,那“一把刀”就是指杀猪行业,香饽饽。女人答应了。这第二婚倒是比头婚强点,但也不过一年的光景。那年年关,大河滩上一户人家养了一头五爪猪,出栏时请来郑屠屠。这种多了一个爪的猪,不吉,遭凶。依乡规旧俗,执刀者必沐浴更衣,披蓑戴笠,脸上抹血,眉心点红。但正值年关的旺头上,明晨又约了户家,郑屠虽知有此一说,但没忌,下了手。诸事停当后,主人好客,桌、碗、椅摆好,热灶热锅,现杀的猪下水陈年的酒。淡黄黏稠、醇香四溢的倒缸酒,郑屠一连大满三碗。回家时,搭乘邻村西水贺家老二的手扶拖拉机。已经能看见自家的信鸽箱了,可就在上村口那孔石拱桥的时候,他却从拖拉机上一头裁了下来,头磕在了石头剪子上,脑壳开了花,带着酒气的血溢满了整一座桥。死了。嫁一个死一个,再嫁再死,且没一个男人让女子巴起肚来,背地就有人开始说了:“没有金刚钻,不可揽这瓷器活。”这风言传遍耒水上下四十里。
有见缝就插的媒婆寻摸进了马村。媒婆长着螺蛳脸,干瘪像咸菜皮似的双耳垂上穿着金镏箍,嘴唇上角有颗痣,痣疣中心撇出两根蟑螂须——据说嘴角挂痣的媒婆,是绝配,但如果再配上两根能摇探四方的触须来,那就是媒婆之王了。天下没有她做不好的媒。从村口寻到村尾,把正在牛栏里看牛的老光棍拽了出来。“你还是个红花乃子吧?”媒婆见面就无不讥讽地说道,“再割两季禾,怕就成了秋天的黄瓜喽!”一句话将男人说得满脸通红,那嘴巴竟抽搐了起来,正想发作,媒婆抢在前又开腔了:“这回好啦,我帮你寻了一门亲,女方可好哩!既漂亮又温柔,既懂理又贤惠,今年才二十,比你足足小了十多岁呢!真的是打着灯笼无处找,嘻嘻……”
天下媒婆一个样,“百货中百客”是她们的信条,她们笃信这个奇形异状的世界没有斗不拢的榫、做不好的媒。反正嘴巴两块皮,既不花钱又不费劲,开口说人话,闭口搭鬼腔;死能说活、假能说真;东边的王三,西边的李四,配不上也非要扯拢一块。媒婆将那男人说得跟在她屁股后面溜溜直转。被别人成天骂着“一双臭大脚冇得鞋配”的男人早已没了非分之念,当即应允。“只是……她下得了蛋不?”家贫自然气短,老光棍于是问道。媒婆挠头弄腰,双指尖从腰兜里捻出一方十字绣手帕往空中那么一划拉,快如飞道:“搞不大肚子都是那两个死鬼的事,怪不上女方。我带她上过乡卫生所,赤脚医生说得有榫有卯,保准有你做爹的!”
一月后,那男的娶了那女的。没花几个钱,老婆娶回家。女子什么都好。既年轻又贤惠,既娇小又温柔,举止也得体,还不嫌他那一间半破茅屋,仅仅是脸长了一点。看相人说了,这是马脸,带杀气,可男人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太需要一个老婆了。
冬天,湘南乡村的夜晚漆黑而阴森。映衬在天幕下的山、树尖、竹梢、耸立的怪石,还有村头连着村尾弯弯扭扭的、闪着磷光的石板路,都像鬼魅一样在黑夜里张牙舞爪来着;黑暗中时有野兔在奔跑,它那小软蹄子像竹竿上吹动的裤筒发出的空洞声在四野急促地响起;而黄麂总是一动不动地警惕地立在远处窥望,准备着一有风吹草动便闪身而去;微风送来冬茅鼠啃噬茅根发出来的细微、低闷的咯咯声;只有耒水的浪涛声是那样的气势磅礴又浑厚亲切……
这对新人与所有新婚夫妻一样,享受着新婚的甜蜜与浪荡。那个被讹言妄语笼罩的马脸女人黑暗中暴露出来的不为人知的温柔总让男人兴奋不已。有一回女人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窃声问道:“你想生几个伢子?”雄心壮志弥补了他身体的单薄,他拍着胸口吼道:“一窝!”像猪产仔一样,一窝至少也得七八个。女人咯咯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