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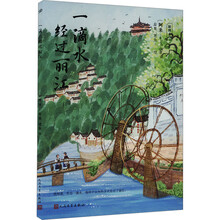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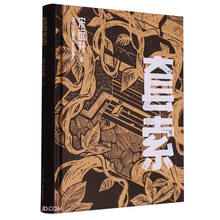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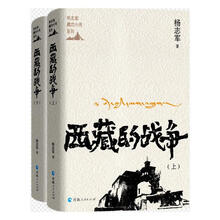
² 茅盾文学奖得主,从川西藏区走向世界的文学大家——阿来,
与《尘埃落定》双峰并峙的史诗巨作《机村史诗》。
² 为阿来赢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
阿来倾注更多心血的满意之作。
² 以花瓣式立体结构,呈现藏族山村变迁史。
以丰沛的诗意之笔,书写时代大潮中孤立无援个体的抉择与命运。
“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² 《机村史诗》(六部曲)之《荒芜》,与神话时代的故乡废墟做最后的道别
荒芜的土地虽然可以重生,时代与命运却早已将世界的面貌完全改变
索波带着四人小队去寻找代代相传的古歌中传唱的“觉尔郎山谷”,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古王国探险之旅。深不见底的神秘峡谷、在黑夜中才能前行的陡峭山道、古王国的废墟中游荡的狼的幽灵……
这个沉睡在传说和歌谣中的古王国会是机村最后的希望吗?
² 偶然间流落到机村的红军战士林登全(驼子),从此和机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新时代来临的动荡中,他和机村人一起度过了一段波澜起伏、令人唏嘘的岁月。
在机村,他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辛勤耕作;在自然灾害面前,他带领着机村人拯救荒芜的土地;最终,土地却不再被需要,驼子孤独地倒在了丰收的麦田里。
“命运就像是一阵旋风,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从虚空里一下就卷起来,把地上的尘土与枯枝败叶都卷入其中,那么强力,那么恣意地飞舞一阵,又从虚空里消失了,只是所经过地方的面貌都已然改变。”
² 特别收录:
² 阿来“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受奖辞;
² 阿来为新版本《机村史诗》专门撰写的代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全新装帧,绚丽撞色设计+典雅烫金工艺;内容全面修订升级。
《荒芜》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创作的重量级长篇小说六部曲《机村史诗》的第四部。在这本书中,机村因为贡献出森林而失去了土地,肥沃的黑土逐渐荒芜,村民们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茫然失措。协拉琼巴、索波等一行四人,启程去云雾弥漫的觉尔郎峡谷,去寻找古歌里林子中飞舞着五彩的鸟群、溪流中流淌着金子与玉石的古王国。村子里,伐木场的工人和村民的矛盾一触即发,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近在眼前。
《机村史诗》(六部曲)是用花瓣式架构编织的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机”在藏语里是种子的意思。六部曲的每一部既独立成篇,又彼此衔连,共同呈现了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这不是一曲旧乡村的挽歌,而是时代巨变下,一个个人的命运故事。
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代后记
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戎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
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
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特殊性的机村,其实也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们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唯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迄今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识见。
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在我写下的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我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
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这部小说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2017年7月11日
荒芜 001
事物笔记:脱粒机 195
人物素描:自愿被拐卖的卓玛 205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受奖辞 215
“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阿来持续为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照亮这些灵魂所需要的仪式写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时代大潮面前孤立无援的个体不致失语。”
——“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授奖辞
“我认为《机村史诗》比《尘埃落定》写得好:《尘埃落定》写藏区,我们或许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的藏区——神的、半神半人的世界;而《机村史诗》写藏区,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机村史诗》比《尘埃落定》难。”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
“阿来的《机村史诗》让人想到一句话:伟大的作品都有一个平静的外貌。”
——作家 马原
“阿来在这里没有标榜和渲染藏区的风土和民俗的特异性的奥妙,而是将这些民俗和风土放在具体而微的语境中追寻它的具体的展开,阿来没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神秘的空间性的无限的展开,而是回到了具体的历史中去尝试思考民俗与风土的具体的意义,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另类的视角再思‘现代性’。”
——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古朴的藏区村落被置于一个大变乱的时代,生出奇异的图像,许多场面成为寓言——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时代的。如阿来所言,此时的‘乡村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中华读书报》年度10佳图书评语
《机村史诗》,其实就是讲人在村庄里的生活,以及人和自然的万物之间的一种无间的关系。
——文学评论家·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