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会飞》:
“众所周知,鸟类从其蜥蜴型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个鞭状的长尾巴,由多节脊椎骨组成。在流体动力学长期的影响下,尾骨逐渐缩短愈合成一块小的骨节——尾踪骨,用以支持呈扇形排列的尾羽。这是鸟类飞翔所必需的,从最早的始祖鸟到所有现代鸟类都有。企鹅也有尾踪骨,这无疑是会飞翔的祖先留给它们的遗产。
“翅膀发达的飞翔鸟类都是把喙插在翅下睡觉的,不会飞的鸟类用这种姿势睡觉是不适宜的。企鹅却用这种姿势睡眠,说明它和飞翔鸟之间有某种关系。此外,飞翔鸟在飞行中要迅速调节肌肉的活动及协调身体各部的动作,所以飞翔鸟小脑非常发达。企鹅恰恰有复杂而发达的小脑,这也被看作是会飞祖先的一个遗迹。毫无疑问,现今的企鹅是由会飞的海鸟进化来的。那么,企鹅究竟何时开始由会飞变得不会飞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的呢?我有这样一个故事……”
下课的铃声响了。
我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娓娓道来的阐述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共鸣,热烈的掌声希望我把关于企鹅的故事讲完……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下课!”科比教授冷冷的声音打断了我正在高潮中的阐述。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他们希望我把故事讲完。我看着科比教授,希望他让我把故事讲完。科比教授带着不满情绪把厚厚的一叠讲义用力在讲台上蹾了几下,就像乡下盖房子打地基夯实黏土,震得讲台上的粉笔灰在从教室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下升起不小的烟尘,像核爆炸一样缓缓升腾。科比教授把整理好的讲义放入咖啡色古董牛皮公文包,低着头,并不看我,起码不是很欣赏我的阐述。
离开教室前,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和科比教授眼光交流的机会,我忐忑地微笑着以示友好和尊敬……不会吧?冷冷的目光回馈来……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月前,他曾经在校园咖啡馆里和我提起即将在北美《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不会飞的鸟类之谜》的学术报告。他还含蓄地暗示,让我帮助他收集关于“不会飞的鸟类”的资料。想到这里,我心一凉,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尽量不想把科比教授的心胸想得太窄。学术上的讨论,个人观点不同。他应该知道我很喜欢他的这门课,很用功……那眼神……异样的,话里有话的,阴暗的,充满不确定的:“咱们走着瞧!”这种眼神太熟悉了……在四川大学,我读本科的地方……不,这里是加州旧金山大学!可我不能不去多想……科比教授这门课我费尽了心思,这是我期待着拿到A,甚至A+的课。它和我下半年奖学金直接挂钩呀!
我从旧金山动物园出来,散步横跨过“伟大的快速路”(Great HW)来到日落海滩。从太平洋深处吹来的海风凛冽、匆忙。上午在科比教授课上发生的不愉快让我开始考虑放弃内心深处的野心:攻破一项前人不曾定论的动物学界难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坚持?一定要和科比教授唱对台戏吗?下次课我就可以拿着一堆的数据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企鹅的祖先不会飞,它们从来没有在蓝天翱翔过,它们是半鱼半兽的怪物。可以吗?我想起科比教授在咖啡馆里找我闲聊时的样子……他即将发表在北美《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学术报告不是正需要我为他收集关于“企鹅不会飞”的资料吗?我可以放弃吗?为了A或者A+……我好像已经听见了同学们的“嘘——”声,还有冈萨雷斯一定会落在我脸上的拳头,还有索菲亚对叛徒的嗤之以鼻。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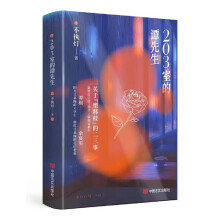




——钱学杰
★贫穷是什么?贫穷就是绞肉机,让你什么完整的都留不下。以前你是块儿肉,有骨头,有筋,肥瘦门儿清。后来被贫穷修理得没骨头,没筋,肥瘦也看不出来,成一堆黏糊糊的肉馅儿了。零零碎碎的肉馅掺和上酱油、盐、高汤、花椒粉、葱姜……再用面把它们包成包子、饺子……蒸完了、煮完了、煎完了,那肉又成了一整块了。可是你发现,不一样了,不是原来的整块肉了;是加工过的,就像红烧狮子头:看起来还是大块的肉,可实际上是肉馅和面包屑,一碰就碎了。
——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