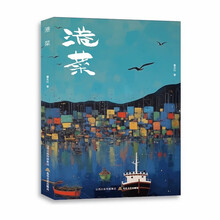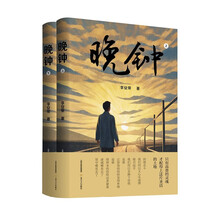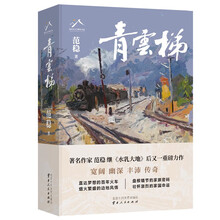活成一棵树
叶剑秀
民国十八年的风贫瘠而空瘦。
刚入荒春,天空一片阴沉灰蒙。干裂生硬的冷风像一群饥饿的飞鸟到处扑棱,掠过波浪似的丘陵,终归也没找到饱腹的食物,像小孩儿一样怄气耍赖,上蹿下跳地打旋儿,好似故意偷懒和撒娇,坠下身子不走了,仿佛非要等来点施舍才肯上路。
枯蒿还没有发芽,挺着瘦弱的身子哧哧发笑,笑风的无知和荒谬。
马中山在路旁槐树上拴了菊青骡子,猴急地跳跃几步,褪下单薄棉裤小解。正当他对着一堆乱石滋得舒坦的时候,瞥见了不远处的土丘下窝着一团东西,那团东西忽然蠕动着折起身子,马中山才看清楚是个人。他不好意思地点头示意,双手簌簌地了裤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在这儿弄啥呢?”
“等人,我和闺女在这儿等人。”回话的声音苍白无力。
马中山再一次打量,原来是两个人:“谁知道还有个女娃呢!”说完转身离去。走了几步,随意回问一声:“荒山野岭的,在这儿等啥人?”
“等北山的刘皮匠,约好今儿个过来的。”
马中山停了下来。
姑娘坐起身来,眼神少气无力地眨巴一下,柔弱无助地倚靠在老人身旁。姑娘一头蓬乱的黑发,脏不拉叽的靛蓝色对襟土布夹衫,不太合体地罩在单薄的身上。姑娘浑浑噩噩看了他一眼,双手夹着膀子瑟瑟打战。
出于好奇,或者是怜悯,马中山抬头巡视四周,哀叹一声说:“天近晌午,如不介意,随我到前面的三里铺吃碗热面,边吃边等。”
父女俩对视,急促地起身,像遇到了神,躬身施礼。
三里铺是个不大的地方,在三条商路的交汇处,既不是镇,也不是村,有一二十家生意门店散落在路两旁,照应着过往行人。
在一家小店,马中山要了三碗热汤面和三个杂面馒头。
父女俩不管不顾,埋头吃得急忙而失态。
老人说:“其实我和刘皮匠也不太熟。他在我们村收过几回羊皮,我托他给闺女找个婆家,约好今天在这儿碰头的。”
马中山叹一声:“这年头,人都顾不住自己,话就更指靠不住了。不瞒您说,我也是做皮货生意的,这个刘皮匠还真没听说过。”
闺女一口咬下去,馒头上就是一个深窝,哧溜又喝了一口汤。
老人看了闺女一眼说:“两天都没进东西了。”
马中山问:“哪有这样嫁姑娘的,不怕遇到坏人啊?”
老人抹一把嘴,望着马中山:“逼得没一点活路了,能给她找口饭吃就行。”
马中山不解:“干吗要交给刘皮匠,在咱这儿找个安稳人家不行?”
老人眼里泛起湿红:“近了麻烦大,远了免得有念想。” 马中山起身结了账:“该上路了。”
分手的时候,老人拉住了马中山:“你是个好人,把姑娘带走吧,俺也放心。”
马中山轻笑一声挥挥手:“我三十大几的人了,有老婆孩子。”
姑娘走上来,羞怯的眼里发出乞求的微光:“俺不求什么。你只当做件好事,再拖就出事了。”
马中山一脸惊疑,摸了摸下巴:“我倒是可以帮这个忙,不会太差。”
老人急身靠近马中山,悄声细语嘀咕一阵儿。
马中山会意,抬腿上了骡子:“三天后,不管事成不成,我都会去你家一趟。”
大叶村叶家的院落里飘起一缕细细的烟雾,晚饭毫无疑问不怎么景气。叶家先前是大户人家,原本是称叶府的,到了叶敬棠手里,变成了老态病牛的模样,气息照样还有,底气已经不足了。唯有残留的这座院落和上房的三间青砖瓦房,东西草棚厢房,算上河滩的三亩薄地,还多少可见曾经的殷实。叶敬棠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爹不成器,把家业抽干了,房子和田地换成烟粉,吸一口吐出来,都变成别人家的了。轮到他体弱多病,能给叶家留条根就不错了,指望挣回以前的家产,他没有那能耐,也不愿去受那份罪。眼下去集镇上喝一碗羊杂冲汤,还隔三岔五接连不上,哪还有工夫去想那乱七八糟的事呢。
孩子的事总得想吧?不想。孩子叫叶青林,人闷话少,木讷笨拙,25了,早过了婚龄。叶敬棠的老婆不知哭了多少次,终归也没哭出个媳妇来。埋怨多了,就招来叶敬棠一顿臭骂:“闷葫芦放不出一个响屁,靠别人按住屁股挤压,就能听个响儿?”
“断了后,看谁丢人。”老婆悻悻地嘟囔。
叶敬棠撂下常说的那句话:“早该断了,笑话不到我头上。仰八叉尿尿,流哪儿是哪儿。爹不管我,我不管儿,不亏不欠。”
马中山走进叶家的那一刻,叶家有了转折和生机。马中山做生意起步时手头紧,买骡子钱不凑手,叶敬棠给过接济,虽说早还了,恩情不能忘。
叶敬棠听马中山说完,该喜不喜,依旧麻木着一张老脸:“哪儿的?”
“北山石岭村的。”
“多大了?”
“19。”
“人咋样?”
“模样还说得过去,个头不小,人结实,到咱家好养。”
“想要多少?多了我可拿不出。”
“好说得很。一口袋细粮,一口袋粗粮。”
叶敬棠的老婆一旁问:“就这么多?”
叶敬棠横瞪过去:“这也不是小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办事还要买鞭炮、贴喜字对联啥的,不置办两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