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卷富有人情味的批评小书,一本“好看”的文学爱好者必读书
▲ 李敬泽诚意推荐,青年批评家岳雯蕞新文学评论集
▲ 关注新世纪文学议题,折射二十年时代变迁
关注新议题:二十一世纪二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全景、新时代的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好人”定义的变迁、长篇小说开头的变化
重读实力作家:冯骥才、梁晓声、金宇澄、王安忆、邓一光、阿来、冯良、叶舟
▲ 新一代文学批评之声,对同业者的鼓舞与呼唤
在新时代的大变面前,之前关于文学的种种阐释、想象与期待都可能失效。新一代批评家,正在超越以往的惯性,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应对文明的差异乃至冲突,迎接新的挑战。
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岳雯向同业者发出鼓舞:让我们共同去爱,去分析。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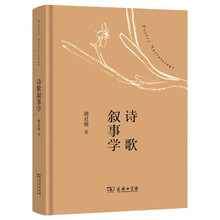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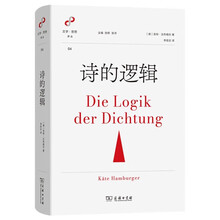






大部分批评家自身其实无法构成这样的国度,但岳雯是一个小小的国度。她的工作、年龄、教育、经历,她的性情和禀赋,使得她自成一体。在文学批评得以生成和生效的各种因素的特定交叉点上,她灌注认真和执拗、洞见和天真、锐利和慧黠、目光远大和家常日用。在喧闹的文学现场中,她正在或已经成为一处独特的批评景观。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