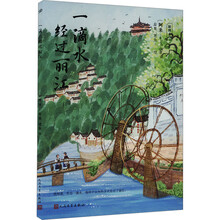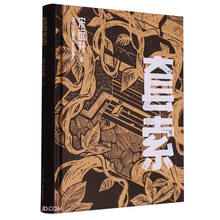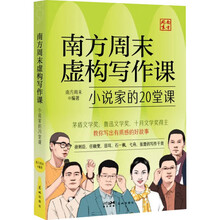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策略问题,也就是在明白“转换”的目的与内涵之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将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与话语范式等转换为当代可用的文论话语资源。党圣元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并非仅仅是一个属于观念认识层面的问题,而更主要地是一个属于学术实践层面的问题。”②我们认为,古代文论是有可能,而且必须转换为现代文论话语资源,其所具备的文论价值才得以最终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同时涉及一个话语重建的问题。但是,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和策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话语重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就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话语重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如杜书瀛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的具体操作方法: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意谓——原作者(或原典)想要表达什么;蕴谓——原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当谓——我们诠释者应该为原作者说出什么;创谓——为了救活原有思想,或为了突破性的理路创新,我必须践行什么,创造地表达什么。郭德茂提出古代文论转换的五种操作模式:一是顺水推舟式,对某一概念或范畴,从新的角度根据时代内容加以填充和推演;二是脱胎换骨式,对一些命题加以新的解释;三是举一反三式,对原有的理论概念进行再次检视甚至反向思维;四是嫁接生成式,通过概念的重构与升华,构成新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形态;五是另起炉灶式,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寻求理论形态的变异与新造。③童庆炳认为,现代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在策略上应该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历史优先原则,即有必要通过科学的考证和细致的分析,尽可能接近古代文论原有的历史语境,恢复其本源性的意义存在,如作者论点的原意、与前代思想的承续关系、现实针对性等;二是“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即以中西和古今两个维度的对话来激活古代文论,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补、互证和互释,从而对古代文论的遗产进行转化,使其能为今天所用;三是逻辑自洽原则,即在对话中达成逻辑的自洽,对话不是各说各的话,而是要有必要的沟通、融合、吸收、交锋、碰撞,要通过对话有所发现,有所创获。①曹顺庆、李思屈从四个方面谈到重建中国文论的路径和方法:一是“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从现代的学术视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对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言说方式的内在文化意蕴进行更深入的发掘”。二是“在对话中凸现与复苏”,通过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形成不同话语之间的“复调式”对白,从而使异质话语达成交流与融合的可能。三是“在广取博收中重建”,广取博收必然形成一个“杂语共生的阶段”,在杂语共生中既与他者交流对话,又确保自身话语的独立性。四是“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重建的最终目的还在于指向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②
总体而论,文论界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策略与方法的思考.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四个层面:一是整理国故、研究传统;二是激活传统、走向创生;三是古今对接、中西化合;四是重建话语、介入实践。我们从这四个层面出发,谈谈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策略的看法。
第一,就“整理国故、研究传统”而言,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对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运思方式、话语体系及其所映照的民族文化心理等进行客观化、具体化与历史化。这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基础工程。这一环节做不好,转换也就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话。在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古代文论的研究区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所谓理论研究,指将古代文论视为一种纯粹的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和民族文化精神的符号载体,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事无巨细、锱铢必究。应用研究则是要通过具体的研究,分辨出哪些概念和范畴已然作古,难以实现或无须转换,哪些概念和范畴同今天的民族文化心理有血脉勾连,可以经过话语的重新阐释获得转化的可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主要可以归结为古代文论话语的应用研究。当然,应用研究不能脱离理论研究,双方应实现辩证的统一,才能夯实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理性基础。有学者认为,一定的范畴与产生它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并不适于文学发展的一切阶段,范畴自身的这种性质是否为我们提供转换的可能性?此外,我们现在对范畴研究的水平是否已经达到了应用的层次?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也是我们在研究“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时必须面对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