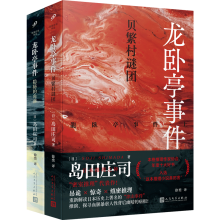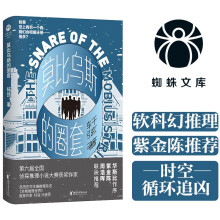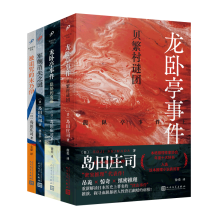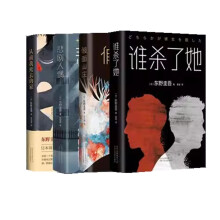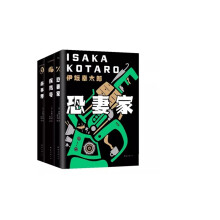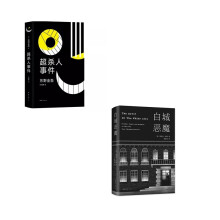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贵和高雅。如同科学和自由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样,高贵和高雅也是人类永远心仪的生存佳境。否定这一点,那就是自甘堕落。而我们半个世纪的文学遗产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
这种堕落当然不是孤立的学术现象,或者也并不完全是研究者们自愿的,而是与整个社会对知识、知识人才、知识行业的强制性轻贱有关。这种轻贱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尽管近些年来,知识被公开声称受“尊重”了,但轻贱知识的旧体制其实并未根本改变,因而知识仍然无法真正尊贵起来。
既如此,文学遗产研究也就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历史性的媚俗和堕落,谈“人民性”就理直气壮,谈高贵和高雅则心虚、羞涩。然而,正如人们对高贵生活的追求实际上早已超出了观念的局限一样,人们对文学遗产的价值体认实际上也早就超出了过去所谓“人民性”的范畴。寻求高贵和高雅,毕竟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的精神动力。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