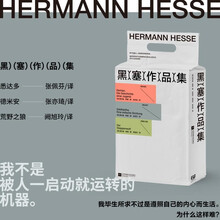福楼拜曾经说过,他想写一本关于“乌有”(nothing) 的书,但《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是他一辈子对抗愚蠢、贪婪和庸俗的火药库里的一个武器。他对他乐于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恶心和恐惧的反应需要对他的性格进行探讨。在不影响这位给世界文学带来不朽丰碑的天才作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深入探索他所角力的情感上的魔鬼为何,因为这有助于确定他与现实世界、他的作品以及他的文化的关系。因为毕竟是福楼拜,而不是别人,创造了爱玛·包法利、萨朗波、弗雷德里克和萝莎奈特,还有他那充满魅力的想象世界。
福楼拜由于报复中产阶级社会所发出的恶意诅咒,可以说大大超乎了客观的水平。他曾提议和几个朋友坐在他住屋的阳台上,看着底下路过的行人并对着他们头上吐口水。他希望他的 《萨朗波》一书会 “惹恼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惹恼所有人”,他甚至宣称,他最想做的就是烧毁整个鲁昂和巴黎。他想把1871年的革命分子全扔进塞纳河。我们不该把这类发自内心的想法看成单单只是一种黑色幽默的表现而已。福楼拜这种压抑的反复发泄行为使这些尖刻脾气的表现有了某种心理学上的意义。从某个角度看,他的憎恨是一种症状:他的恐惧症和所有这类病症一样,都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卫行为。比起它所隔离的恐惧,它带来的困扰更少。恐惧症患者的压抑行为,不管是害怕过桥或是一看到资产阶级就出不来汗,都是一种防御性措施。然而,这种防御策略注定要失败:福楼拜的窒息和呕吐发作,即使实际情况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却也说明了他无法掌控自己焦虑感觉的事实。想要变成《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或《布瓦尔和佩库歇》里的佩库歇,不会只是创作文学的一种有用策略而已。对福楼拜而言,资产阶级的儿子和兄弟,这是他最糟的梦魇,但同时似乎也是他最深层的愿望。
对付恐惧症的策略有两种,福楼拜两种策略都使用。第一种是尽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借此和庸俗之辈隔开,以免受到他们的污染。他在巴黎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学界朋友共进晚餐,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社交行为,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受到资产阶级污染的人。第二种是采取反恐惧症的姿态,直接去面对引起他恐惧不安的因素。他坚持不懈地关注那些 “无教养”的同胞,勤奋地收集他们的言论,记录他们的态度,并不断地解剖他们的行为,是直接面对敌人的英勇行为。
福楼拜因此是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作家,甚至对可能最适合他的补救措施也感到不安。他内在最矛盾的冲突点,以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来,指向了当时著名精神科医生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称之为“生殖事务”(la chose génitale) 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一切原因中的主要原因。诚然,对福楼拜而言,生殖事物的问题正是他一辈子的困境所在,他从未解决对性的不协调感觉,他总是无法确定,要拥抱还是抗拒诱惑。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在他身上放荡逸乐的倾向经常会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写作。他从一开始和科莱小姐交往以来,就反复感到独处的冲动。科莱在年纪上比他大11 岁,在情场上身经百战,不知道已经睡过多少张著名的床铺, 和他认识时美貌仍在,不能说对他没有性的吸引力。但他会经常不客气地跟她强调,对他而言,爱情必须臣服于艺术的要求。“在我看来,爱情不能摆在生命的前台,它必须摆在后头才行。”他为了和这位 “可爱的缪思”保持距离,就不断鼓励她要爱艺术多于爱他。1843年,福楼拜21岁,当时著名的雕刻家普拉迪耶 (James Pradier)曾建议他去好好谈一场恋爱,他告诉年轻的密友勒普特文 (Alfred LePoittevin)说: “这个建议很好,可是如何进行呢?”当时普拉迪耶的妻子年轻貌美,且又自由开放,和丈夫分居,此时成为福楼拜的女友,两人 “短暂”交往了一阵,福楼拜认为 “短暂的”恋爱适合他。他承认: “我需要恋爱,但我不会去做,那种正常的、规律的、维持得好好的稳定两性生活会让我失去自我,会干扰我。我应该重新进入活跃的生活状态,进入身体的现实,事实上是常识,而我每次尝试的时候,都会带给自己伤害。”
因此,为了满足性欲,同时又要尽量保有隐秘的个人生活空间,他偶尔会去妓院买春解决。他在写给科莱小姐的一些比较随意的信中就称赞妓院这个古老行业的迷人之处。他每次一想到婚姻就害怕,一想到要做父亲就浑身不自在。当科莱小姐暗示说她可能怀孕时,他恳求她去堕胎。他很高兴自己住在鲁昂,科莱小姐住在巴黎,这真是个美妙的距离——至少他觉得很美妙。福楼拜毕竟还是少不了她,其中有几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他写给她的信件可以说结合了色情告白 (“你大叫道:‘咬我,咬我呀!’你还记得吗?”)、关于写作的精彩小论文以及对文学的信仰告白。1849到1850 年之间,他去埃及和近东旅行了18个月,这真是一趟性狂欢之旅 (包括几个雇佣的漂亮男孩),一路上性交个不停。其中最猛烈的一次是和一个叫做哈内姆 (Kuchuk Hanem)的著名妓女,他写信回来给几个亲密好友——除了母亲之外——巨细靡遗地报告和这位妓女的猛烈交媾过程 (“我疯狂地吸吮她”),当然还有其他更猥亵的文字描写,此处不便一一详述。
福楼拜所写的一些色情的信简,在他所出版的作品中算是比较不引人注意的部分,说明他未完成的童年事业持续存在。他在小说中会大玩俄狄浦斯情结之主题的游戏,也描写杀父,有时相反,不听话的儿子被无情的父亲杀了,以及母爱和肉欲的危险混合。在现实生活中,他很难将这两者分开。拜伦曾大笔一挥写到,要像爱母亲和情妇一样爱意大利。福楼拜有一个英年早逝的妹妹,名字叫做卡洛琳 (Caroline), 他们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要好,好得有点超乎寻常, 甚至有点色情的风格 (“我要好好把你吻个痛快!”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她当时18岁,福楼拜21岁)。和其他人一样,他的思想走到了行动跟不上的地方,但他确实把它们全部写了下来。他是个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他对天主的不敬非常极端。比如他幻想在一间意大利教堂里做爱:“黄昏将晚的时候,能够躲在那里的告解室后面,在人们点灯的时候就地狠狠干一趟,会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他在尚未真正从事写作之前,曾说想写一篇故事,描写一个男人对一个追不到的女人的爱情,他说这篇故事会让读者惊吓得发抖。他说, 他知道有些欲望他不敢去触碰,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妹妹,还有另一个:埃丽莎·施莱辛格 (Elisa Schlesinger)。
他的确曾经很认真地坠入过一次情网,而且从他留下的文字判断还始终相当地忠诚——以他自己的方式。除了这次之外,还有一次传闻中的恋情,据说他当时也着实很 “认真”过,对象是他外甥女卡洛琳的英文女家庭教师茱丽叶·赫伯特 (Juliet Herbert),只可惜这桩恋情因缺乏证据而无稽可查。他对施莱辛格夫人的这桩恋情则是证据确凿,施莱辛格夫人的丈夫是个和蔼、精明、不择手段的生意人,福楼拜在特鲁维(Trouville)海滩上认识她的时候才15岁,而对方已经26岁——刚好是他和科莱小姐在年龄上的差距。埃丽莎·施莱辛格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体态丰满,经常露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福楼拜完全没有机会,因为她对她那位喜欢拈花惹草的丈夫非常忠实。
他从未得到她,可却也从未忘记她。他早年写过一篇自传式的作品叫做《狂人回忆》 (Mémoires d’un fou),内容即是描述他如何爱上她的过程。“玛丽亚,”他如此称呼她,“有一个小孩,是个小女孩,她很爱她,常常爱抚她并不时亲吻她。”他真希望自己能 “接受到其中的一个吻”。玛丽亚 “自己喂小孩吃奶,有一天我看到她解开上衣,露出胸部给小孩喂奶”,这件事的确在特鲁维尔海滩上发生过,这一幕令他永难忘怀。“她的胸部既圆又丰满,褐色的皮肤,我还可以看到那细嫩皮肤底下淡蓝色的血管。我之前从未见过女人的祼体。哦! 看到那只乳房使我陷入了奇异的狂喜,我想用我的眼睛吞噬它,我多么希望只是触摸它!”他幻想自己激烈地咬住它,“一想到吻她的胸部所可能带来的色欲快感,我的一颗心都快融化了”。
三十几年后,在《情感教育》 (1869年出版)一书中, 对故事男主角弗雷德里克而言,埃丽莎化身为半是母亲半是令他渴慕的情妇之混合人物,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中情人。三年后,福楼拜写了一封动人的信给埃丽莎,信中为他没有早一点给她写信道歉,有点可怜地把疲劳作为理由,“我的人生越是往前迈进,越是感到悲哀。我正回到以前全然的孤寂状态。我为你儿子的快乐献上我最虔诚的祝福,我视他如我自己的儿女,我热烈拥抱你们两人,我要拥抱你多一点,因为你是我永远的爱人 (ma toujours aimée)”。埃丽莎是个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但对她的情况,福楼拜愿意做个例外。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