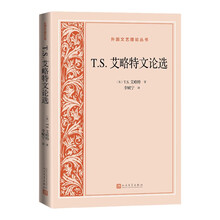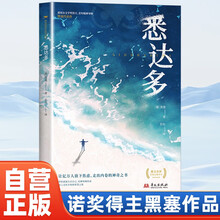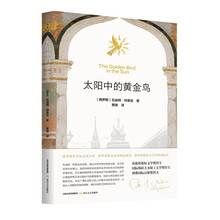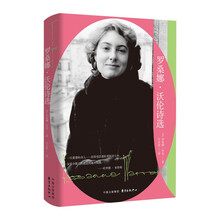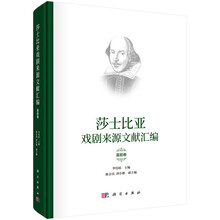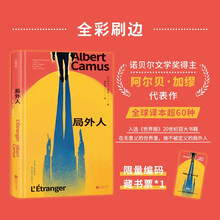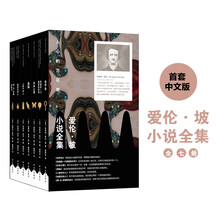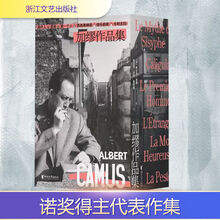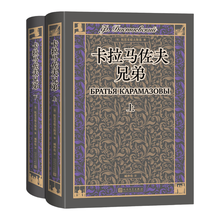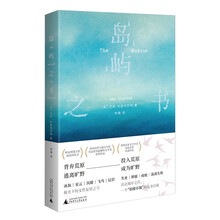《海外华文文学的跨界研究》:
《望月》里的女主人公虽身为艺术家,感情也绝非一张白纸,但意识深处仍摆脱不了中华传统女性关于稳定与名分的期待。她与“牙口”发生关系的同时,也暗藏着关于天长地久的一丝企盼,但猝不及防的现实无情地撕碎了她的期望。望月发现“牙口”暗地里与一个男人长期交往的场景构成小说极富戏剧冲击的一幕。一方坦然承认,而另一方却无法以同样的坦然接受眼前这个事实,生生地揭开了中西文化思维中关于两性关系与性取向认知上的裂罅。尽管他们曾经最为亲密,却始终无法相互理解。
在长篇《交错的彼岸》里,一场给蕙宁命运带来巨大转折的风波,最初仅仅是一些中西文化交往差异的微小事件。谢克顿教授在作业中写评语、送蕙宁回宿舍等举动引发了无数的流言,使得原本师生之间若有若无的朦胧吸引被粗暴“定性”为既成事实。谢克顿教授送蕙宁回女生宿舍,在西方看来是一种绅士风度的社交礼节,但中国内地保守闭塞的年代却只能招来风言风语。文化上的代沟促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如同谢克顿的自述:“我诸如此类的自以为是,以及我对中国国情的麻木不仁,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到了温妮。”而对流言产生怀疑的谢克顿太太,看见蕙宁与自己的丈夫在办公室相拥而立的一幕,便将一切闹得满城风雨,话语中体现出的种族优越感,根本不顾是否会伤害蕙宁的感情。这种举动尽管出自女人的自卫心态,效果却适得其反。谢克顿与蕙宁的相恋,从一开始便是文化误会引发的结果,中西文化思维的差异如同隔在他们中间的一道无形的鸿沟,他们之间并没有达成真正的相知与理解。如果没有谢克顿太太的捕风捉影,这段关系或许就仅停留在朦胧阶段,终将无所交集。而彼此之间精神世界无法跨越的隔阂,最终也导致了两人的分道扬镳。
同样是《交错的彼岸》里,因为不了解内地矿区现实,彼得在撰写《矿工的女儿》一书的爱情故事当中,许多观点与视角仍摆脱不了西方本土意识的影响,他笔下的中国无法脱离西式文化的烙印。他的西方理想主义色彩使他并没能真正了解内地中国的现实。《矿工的女儿》当中描绘的情节,以及彼得自身的情感经历,正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本书在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眼中,即不管是沈小娟还是后来的黄蕙宁看来,都带着一厢情愿的荒谬,是西方人想象中的,脱离了现实本来面目的中国。这里仍反映了某种隔膜的存在,尽管彼得前往中国可以跨越地域上的千山万水,却跨不过内心这层无形的距离。从表面上看他近距离接触到中国,与当地的人们同饮共食,但思想上他仍旧隔离在这片土地之外。这种隔阂源自文化传统与思维深处的差异,也来自西方文化中习惯性地站在自身经验立场上对“他者”的误读。
在张翎的另一部长篇《邮购新娘》里,中国女孩“路得”与约翰·威尔逊牧师的关系,更体现着宗教背景下中西观念思维的碰撞。作为被外国传教士收养的中国少女,“路得”虽然从小在教堂长大,并且受洗成为基督徒,然而她的灵魂与意识毫无归顺的迹象。宗教对这个中国少女而言并不能带来拯救,而只能成为精神的禁锢。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路得”的行为异常出格,思想则离经叛道,不仅敢于在传教士面前公然对《圣经》质疑,而且也罔顾一切宗教世俗伦理,对收养她的约翰·威尔逊牧师大胆表露情感乃至欲望。女孩以一种原始、野性、未经教化的“无知无畏”的姿态,打破东西方一切宗教世俗伦理禁忌,真正地只为自己而活,无论与中华传统伦理思想还是与基督教宗教意识都格格不入。在她与约翰牧师的对话中分明体现着这种鲜明的自我意识,这种超脱文明的,来自本能的原始的实用主义思考。她问《圣经》里的路得是先爱上了丈夫才爱上丈夫的神,这在西方基督教观念来看几乎构成“异端”的嫌疑,是虔诚的宗教精神不可能容忍的。约翰·威尔逊牧师依靠宗教收留了这个中国女孩却无法真正用宗教感化她的心。他们之间无可避免地产生文化上的断裂,而在鸿沟之上站立着的,不仅是宗教中的上帝,更是代表世俗伦常监督者的那个“上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