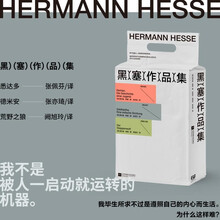们的简短提及并没有吸引中国的人文学者以及广大观众的批评和学术关注。当然其中的原因有点复杂: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更多的是政治上和实用主义上的原因。因为在当时,普通人,甚至包括知识分子,可能会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有点脱节,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他的作品,更不用说欣赏和讨论它们的美了。他们最需要的是像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这样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家,因此他的社会问题剧最受重视,也最切合中国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当时最具进步性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期刊《新青年》在1918年(第4卷第6期)推出了一期特刊,即“易卜生专号”,这实际上也是该杂志推出的唯一一期外国文学与戏剧专号。在那期“易卜生专号”中,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发表了长篇文章,探讨易卜生及其作品在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但是他们却全然忽视了莎士比亚的存在和影响。确实,在新文化运动中,莎士比亚未能得到上述杰出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推介,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莎士比亚虽然在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的英语系得到教授,但多少有点被“边缘化”了。
正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启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和表演。中国作家和戏剧导演本应从莎士比亚那里得到更多的灵感,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由于他的作品似乎有点远离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人们需要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来帮助他们改造旧社会。因此,易卜生所能给的启示自然比莎士比亚所能给的启示更多,前者不仅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转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但是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已经逐步有了一大批莎士比亚学者,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不仅在大学课堂里讲授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同时也著书立说,形成了中国的莎学。但这些莎学研究者大多在一个有限的学术圈内发出声音,并没有对人们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此外,他们很少与国际莎士比亚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声音依然相当微弱。但是毋庸赘言,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并使用世界上仅次于英语的最强势语言——汉语的大国接受和传播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毕竟对其成为世界戏剧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当然,莎士比亚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接受和传播也为莎剧成为世界戏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莎士比亚与亚洲》专题研究文集主编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所概括的:“本书的两个主要假设对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首先,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亚洲和亚洲的影响力,更广泛地表明了莎士比亚的观点。其次,莎士比亚是一个引发诸多著述的视角,据此可以揭示亚洲文化的特征。”(Hart,2019: Introduction,3)这也就说明,莎士比亚与亚洲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也有着互鉴和互释的作用:莎士比亚在亚洲有着众多的观众和巨大的演出市场,他的亚洲之旅不仅受益于广大文学读者和戏剧观众,也受益于戏剧和电影导演的改编。反过来,莎士比亚剧作的引进对于繁荣一个国家的文学和艺术也能起到极大的刺激作用。因此,正如该文集主编所意识到的,莎士比亚与亚洲的关系是双向的:莎士比亚的剧作给亚洲文学艺术的繁荣以启迪和推进,亚洲的文化市场也对普及莎剧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在这方面,印度的宝莱坞制作的一些改编自莎剧的电影对于莎士比亚在印度的普及和传播尤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许多电影观众对莎剧情节的了解无须通过阅读其剧本或观看其剧场演出,仅仅通过观赏宝莱坞电影就可以达到。当然,其中的误读和误解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正好印证了一句名言:在后现代时代,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此外,根据莎剧改编的宝莱坞电影也为莎剧赢得了巨大的市场①,推进了印度电影的国际化进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