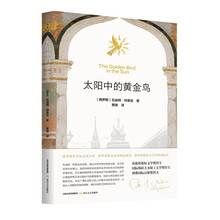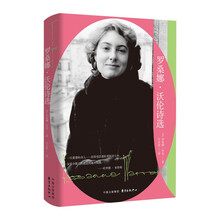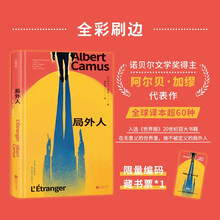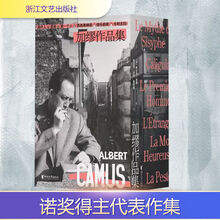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荒诞的游戏:西方现代文学十八讲》:
作家的文体是作家存在的根据。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自在的文体浑然天成,或像大理石玄武岩自显古拙,或像天然钻石流露其光华。它是语言在语言中的上帝的感召下到达的一个自足的领域。当到达这个别开生面的领域之后,语言中的上帝就回到了它混沌的自在状态,以使语言充分开放自身,无论在局部或整体,都呈现超凡脱俗的结构之美。这样的结构之美是通过作家处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在传统小说那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其主流是模仿的“反映”,而在现代文学中,“反映”的可靠性被质疑。因为语言哲学和语言美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即现实。这种认识的革命性,是现代小说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普鲁斯特的文学观中是再明显不过了。至于对隐喻和象征的处理方式,以及它们获得的本体地位,则更说明了语言即现实的真理性。
一般来说,隐喻起源于观念、意义,或者说隐喻是观念、意义对美的意蕴的要求,也是美的意蕴对观念、意义的生成。艺术中的隐喻总想跨越形而上的门槛,观望并拥抱栩栩如生的形而下世界,回归素朴的自在。素朴是形而下世界的“在”,而不是观念与意义浸入之后的“在者”。隐喻自己不能表达自己,因此,它需要借助文化的积淀、心灵处理支离破碎的世界的关系及某种逻辑推力来表达自己。所以,隐喻既来自文化传统,来自文学艺术和语言的历史,又来自心灵的天赋能力。
在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心灵的丰富性和处理一切观念与事物的逻辑能力以及心灵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着隐喻的创造。可以说,没有隐喻在天赋能力推动下的生成,就没有文学艺术的深度构造。不管隐喻的创造是建构式的,还是解构式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建构还是解构,都意味着新的隐喻的生成——尽管有时候是不自觉的。这是语言的决定。语言在对世界(这里的世界包括文学艺术中的世界)的命名过程中,即使是所谓客观的描述,也同样包含着隐喻的生成。这里说的隐喻,自然指那种广义的隐喻,它包括观看的心理习惯、直观的语言形式自带的隐喻,也包括语言符号自身的节奏、音声、调式、形色等新滋生的隐喻。
那么,隐喻与象征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在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时,回避这种关系就不是专业的阅读。安德列·莫洛亚说:“通过揭示某一陌生事物或某一难以描写的感情与一些熟悉事物的相似之处,隐喻可以帮助作者和读者想像这一陌生事物或这一感情。当然普鲁斯特不是第一个使用形象的作家。对于原始人形象也是一种自然的表达手段。但是普鲁斯特比同时代任何作家更加理解形象的‘至上’重要性;他知道形象怎样借助类比使读者窥见某一法则的雏形,从而得到一种强烈的智力快感;他也知道怎样使形象常葆新鲜。”普鲁斯特在《在斯万家那边》中也写道:“不用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搏动着的,一定是形象,一定是视觉的回忆,它同味觉联系在一起,试图随味觉而来到我的面前。只是它太遥远、太模糊,我勉强才看到一点不阴不阳的反光,其中混杂着一股杂色斑驳、捉摸不定的漩涡。”
形象肯定是重要的,没有对形象的探索就没有《追忆似水年华》。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对形象的探索重要的并不在于单纯的形象,而在于形象本身是否符合文本有机和谐的统一性。还有,在语境或文本的结构中,单一的形象之构成只不过是一个出发点。一般情况下,象征直接起源于形象。单一的象征起源于单一的形象。现代文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在文本结构中,单一的形象和整体的形象融为一体,创造单一的或整体的象征,上升为复杂的、高度形式化的隐喻。而在传统文学中,形象的塑造都是有明确目的并为内容、为角色的塑造服务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