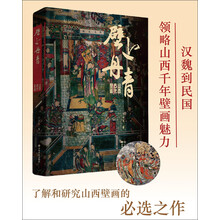《纳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典礼的仪式意义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所有的典礼重点都放在典礼作为一种庆祝某项工作完成以及突出氏族祖先伟大之方式的功能上。名义上是促进多产和繁荣的典礼是在礼堂里铺好新地板时举行的。在这一场合,绝大多数信息提供人都说此典礼是“为新地板而举行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能意识到典礼的仪式意义或对其感兴趣;但即使是这些少数人也不是对典礼的魔力效果,而是对其秘传的图腾起源——即有关氏族荣耀的事情,氏族的骄傲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有关它们的图腾祖先的细节上——感兴趣。因此,整个文化是由对壮观场面的持续强调和男性骄傲的精神气质而塑成的。每一个趾高气昂、大叫大嚷的男人都是在表演,以向自己和他人确证自己拥有某种威望这一事实,而这种事实在此文化中几乎没有正式的认可机制。
如果不对成年仪式的精神气质进行描述,那么对礼堂生活的记录是不完全的。在其他文化中,我们会认为那些训导者是既尊贵又严峻的;在痛苦的割礼过程中,他们会向年轻的受礼者灌输斯巴达式的对痛苦的坚忍态度。这一文化具有很多看上去与这种苦行的精神气质相配的因素:在某些日子里,受礼者和施礼者都不能吃喝;在某些场合,受礼者要喝污浊的水。而且,此文化还包含着一些因素,使受礼者看上去是在通过一个灵魂的危险阶段。他不能用手接触食物,他要经历一场带有仪式洁净意义的彻底清洗;而且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施礼者在保护受礼者免受危险的污染。
但实际上,成年仪式的精神既不是苦行也不是谨慎,而是不负责任地以强凌弱和装腔作势。在切割过程中,没有人关心那些小男孩是怎样忍受痛苦的。如果他们尖叫,施礼者就会去敲起锣来盖住他们的声音。小男孩的父亲也许会站在一旁看着整个过程,时不时按惯例说上一句“行了吧!行了吧!”但没人理会他。手术的操作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展示他们的技艺,将受礼者的扭动和抵抗看作对自己技艺的贬低。观看者则沉默地、我想是带着些许“恐惧”地看着这种与日常的戏剧化兴奋场景迥异的痛苦场面。有些人则显得很开心。
在成年仪式的其他阶段,由一些很乐意做这事儿的男人们来充当痛苦的施加者,他们是带着一种嘲讽的、恶作剧的态度做此事的。喝脏水就是个大恶作剧,可怜的受礼者被骗着喝下许多脏水。在另一场合,他们的嘴被一块鳄鱼骨撑开,让人“检查他们是不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尽管在此阶段对他们并没有任何食物禁忌的规定,但检查的结果毫无例外地是说发现他们的嘴不干净;骨头被突然戳进了此男孩的牙龈,使牙龈出血。然后此过程要在下颚的另一边重复一次。在进行仪式性清洗时,受礼者已部分愈合了的后背被擦来搓去,并被不断地泼上冰冷的水,直到他们又冷又痛地抽泣不止。仪式所凸显的是使他们痛苦更甚于使他们洁净。
在隔离期的第一个星期,受礼者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这类严酷的恶作剧,每一种恶作剧都有一些仪式性的借口。而此举在其文化的精神气质方面更颇具意味,即对受礼者的折磨被用作一种语境,在其中,不同的施礼者群体可以提出种种足以自傲的方面来打击对方。当某个半偶族的施礼者觉得受礼者在其所能承受的程度内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折磨,可以省略某一仪式程序;另一半偶族则开始嘲讽对方那些仁慈的施礼者是害怕自己干不出什么漂亮的折磨手法来;于是心怀恻隐的那一方便狠下心来,在实施各项仪式程序时分外添上了几分残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