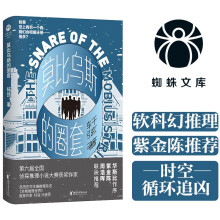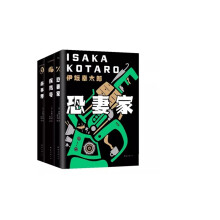壹 民族考古学研究
中国民族考古的开拓者
宋兆麟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的考古学、民族学兴起较晚,都是近代从国外引进的,其初是各自发展的,如考古学强调田野考古,重视遗迹研究。民族学也强调实地考察,编写调查报告,但忽视物质文化或民族文物,这一点至今都是文物工作的软肋,民族文物工作是当今文物工作的薄弱环节。在20世纪中,著名学者吴泽霖已关注民族文物,曾在贵州举办过《少数民族文物展览》,还*先建议中国民族博物馆,与此同时,林惠祥在厦门大学、杨成志在中央民族大学、冯汉骥在四川大学,还有人在中山大学都抓了民族文物研究,有的地方还建了博物馆,这是老民族学家的卓识远见,功不可没。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时间从事民族考古研究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重视民族工作,如开展民族调查,编写民族史志,收集民族文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中也出现了一批专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专家还关注民族与考古研究,这就要*提李仰松先生。
李先生是参加民族调查的*早的考古学者,先去云南佤族地区,后来去滇西北调查,*后又去海南省黎族地区调查。留下许多作品,而且有特点。如他参与编写的《20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考古学进行研究,这是一般民族调查报告所没有的,是学术上的突破。
考古学是研究人类早已遗失的文化,通过遗存和遗物复原历史,有些能说明白,有些就说不明白了,如人们说扳指是钩弦的,其实民族学说它是护手指的;汉代有二牛三人犁,解释多种多样,其实云南农村还在使用此法,是二牛抬杠,由一人牵牛,一人掌辕,一人扶犁。类似例子很多。说明考古学有一定局限性。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学问,其中的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建国之初,我国有母系制残余的“女儿国”,有父权制的*龙族,有阶级社会初期的佤族,还有凉山彝族奴隶制,西藏和西双版纳的农奴制。上述事实说明,民族学研究活的历史,其中有“活的社会化石”,对研究考古学有重要意义。李仰松先生正是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接上头绪的**人,这一点在中国是公认的事实。
我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后来分配在考古专业。当时既主攻考古学,
也学一点民族学,在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林耀华先生的民族学课程时,就由李仰松先生辅导,有时去中央民族学院上课,也是由李先生领队的。他虽然没直接给我讲过课,但我是将他当先生的,事实上许多民族知识都从李先生处得到的。我们师生关系不错,记得还拜访过李先生家,他讲授不少民族考古学知识。常言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自认是努力的。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十个月广西民族调查,回校后还在临湖轩向陆平校长做了汇报。记得我还说过“下乡十个月,胜读三年书”。陆校长批评说:“下乡调查很重要,但学生主要是读书。”我认为他说的正确。后来参加了洛阳王湾考古实习。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我又赶上了从事民族考古的良机:1961年暑假,国家文物局请翦伯赞等专家赴内蒙古考察,事后专家提出,中国民族地区正在翻天覆地变化,旧东西即将淘汰,抢救民族文物为当务之急。国家文物局接受了上述建议,又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主抓此事。馆领导认为我年轻,又有民族调查的经历,就安排我担任抓民族文物抢救工作。自1961年起,我每年都在民族地区生活,先后对内蒙古鄂伦春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四川小凉山彝族、云南泸沽湖纳西族作了详实调查,征集大量民族文物,后来又赴东北、西北、西藏和海南民族地区考察。这些工作类似上了一所民族大学的专业课程,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收集了大量史料,使我终身受益。我的治学活动,有人反对,说我是“考古学的叛徒”,我对此并不在意,历史会有公论的。也有很多人支持我。在20世纪70年代杭州考古会议上,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表示调我去当《考古》杂志的编辑,我不知可否,征求苏秉琦先生意见。他坚决反对,还说:“现在在全国找《考古》编辑,找一千个人也不难;找搞民族考古的人就难了。现在考古界有‘南汪(宁生)北宋’之说,就是对你们研究工作的肯定,尤其是你,在博物馆有一定优越条件,必须坚持搞下去。”苏先生上述鼓励的话,消除了我在民族考古道路上的疑惑,于是我又坚定的从事民族考古工作了。除进行民族调查,完成多卷本《边疆民族调查》著述外,又完成了《民族文物通论》《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古代器物溯源》等专著和论文写作。过去,有关“民族考古”含义曾发生过论战,当事人曾建议我表态,我没有介入。今天我想说,民族考古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本文说的民族考古基本如此;另一种是民族地区的民族考古,从事此类工作的应该是在边疆考古**线的考古学家,我敬仰他们,祝福他们,而不能入伍,这是工作环境所限,无可奈何。其实,两者研究对象基本相同,方法也类似,共性较多,把他们都纳入民族考古也是可行的。有幸退休后遇到大量东北亚民族古籍,这才研究当地民族史,写了一些文章,出版了《蹴鞠:中国古代的足球》《唐代渤海国医疗画资料集》《潘家园访古地》等书。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做了一点工作,但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有不少恩师是不能忘却的,其中就包括李仰松先生,他是中国民族考古的开拓者,也是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领路人。
民族考古学现状与展望
黄建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依靠常识和历史文献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身上解读出的信息有限。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把出土遗物与相关民族调查资料进行类比有助于解读出土遗物的用途,这种方法逐步被一些考古学者运用。民族学与考古学看似没有联系的两个学科被结合到一起释读考古资料,国外学者把这种做法称为民族志类比或民族考古学。
对此,我国考古学者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赞同民族考古学的提法,认为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的学者则不以为然,认为民族考古学实则是民族志类比,它只是丰富了考古学研究手段的一种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缺少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提出要取消民族考古学。当然更多的考古学者虽然未必认同民族考古学的提法,但是都赞成运用民族志类比来解读考古材料。夏鼐曾说过:“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们应该以主人翁的身份来利用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资料和理论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
笔者赞同夏鼐的看法。1949年至今中国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70多年积累起来的考古资料需要认真地解读,解读考古资料离不开民族学,如何利用好民族学为考古学服务成为今后建设民族考古学的关键。笔者认为,建设民族考古学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先要充分认识到民族志类比的作用,厘清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完善民族志类比推理方法,增强用实验手法检验类比推理合理性的意识,在提炼适合于解释考古遗存的概念方面进行探索,使民族考古学成为解读考古遗存功能的重要方法和阐述考古学文化现象的基础理论。
一、充分认识民族考古学的作用
民族考古学对考古学*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民族志类比方法,它不仅为阐释考古
遗存功能,从考古遗存中解读出先民的精神文化乃至过去社会的制度文化提供借鉴,而且还为解读复杂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提供概念。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民族考古学的作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史前遗址出土过不少带U形槽的石器。这类石器长度多在10厘米左右,其宽平表面上有一道或多道U形凹槽,考古学者多称之为磨石、砺石、石磨具、沟槽器和有槽磨具等,认为它们是研磨工具。但是从这类石器多数是用角岩、滑石、板岩、千枚岩和云母变质岩等制成来看,它们显然不适合做研磨工具,所以上述推断是“望形生义”,认识始终不得要领。美国民族学者在对印第安人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印第安人用类似带U形凹槽的箭杆调整器来矫正不平整的箭杆。他们把不平直的箭杆放在加热过的箭杆调整器的凹槽中来回拉磨,使得箭杆变直和光滑。考古学者把两者造型类比后,推断史前遗址出土的U形槽的石器也能够起到矫正箭杆的作用。有学者作了相关实验证明U形槽石器的确能够起到矫正箭杆的作用。这是通过民族志类比阐释考古遗存功能的成功范例。再比如,半坡遗址中作为瓮棺葬具的尖底瓶以及长颈壶的口部在埋葬前就被打破。考古学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可以从民族志记载中的类似现象中获得解释这个现象的线索。斐济人认为假如日用斧头或刀子由于长期使用而损坏或折断了,则它们的灵魂很快就飞去为神服务。据此,把尖底瓶和长颈壶口打破看作毁器行为,毁器的目的与斐济人的精灵崇拜观念相同,让被打破的尖底瓶和长颈壶的灵魂去为死者服务。可见民族志类比有助于揭示考古遗存背后的精神文化内涵。不仅如此,民族志类比还有助于透视考古学文化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元君庙墓地是仰韶文化的一处典型墓地。考古学者完成元君庙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分析后,把该墓地与北美易洛魁氏族、中国云南宁蒗的普米族和永宁纳西族等的成丁礼、丧葬制度和亲属关系等资料作了类比,认为元君庙墓地是由一对实行对婚的氏族——部落的两个墓区构成的墓地,每个墓地代表一个氏族,它们各由若干个家族墓构成,家族墓是由具有血亲关系男女多人合葬墓构成的。这个结论让大家看到该墓地所反映的丧葬制度,考古界对此评价甚高。这个实例表明民族志类比是从出土实物中解读出过去社会制度的有效途径。其实,民族志类比还有一个功能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能够帮助考古学者在发掘现场中辨识遗迹性质。例如,考古发掘中常常发现面积不大呈不规则圆形的没有柱洞的原生红烧土面,红烧土面厚薄不一,考古学者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汪宁生在民族调查中发现西双版纳景洪曼勒傣族群众常常在固定地点烧陶,时间长了该
地面上会形成小面积红烧土,*厚的可达10厘米。他认为依据这个事例可以推测上述原生红烧土面很可能是露天堆烧陶器的遗迹。当然要确认这类原生红烧土面确实是露天窑遗迹的话,还需要辅证。由于这类“窑”的焙烧温度不高,陶坯在氧化焰中焙烧而成,所以烧成的陶器表面颜色不纯而呈现斑斑驳驳的红色或红褐色等,陶器表面多有无意识渗碳留下的黑色斑块。如果能够重视这一推断,以后只要发现类似红烧土面,应当在同一文化层中寻找有无质地疏松、颜色斑驳并有黑斑的红陶片,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红烧土面解释为露天堆烧陶器的露天窑址遗迹。民族学对考古学的另一大贡献是为阐释复杂考古学文化现象提供理论支撑。墓葬是内涵比较复杂的考古遗存,考古学者能够解决墓地环境、墓坑排列和规模、随葬品质与量、死者性别和年龄、墓地时代和文化属性及墓葬分期等问题。限于学科特点,考古学者无法说明其中很多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一般读者无法从这个“见物不见人”的成果中窥视过去社会面貌。但是民族学给考古学提供了解释这些文化现象的理论。位于苏北鲁南交界处的苏北一侧的花厅墓地,处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南部边缘,也是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北边缘。该遗址经过四次调查发掘,共清理了87座墓葬。这个墓地分南北两个区;墓分大中小三型;南区只有中小型墓而北区有大中小型墓;随葬陶器有五种风格,分别是大汶口式、大汶口 良渚折衷式、大汶口 薛家岗折衷式、良渚式、薛家岗式。这些墓中,死者头向朝东;超过1/3的墓随葬猪;大墓随葬的玉器种类和数量不多而随葬的陶器数量很多;大墓与中、小型墓集中在同一个墓地;有的大中型墓中埋葬多个死者;南区只有很少量良渚式陶器,而北区不仅有大汶口式陶器而且还有大汶口 良渚折衷式陶器和大汶口 薛家岗折衷式陶器。从民族学上讲,花厅遗址处于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相当于某个文化的边区。文化边区意味着这里很容易出现涵化。涵化是指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接而发生的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在花厅,大汶口人死后葬在南区,良渚人死后葬在北区,看似泾渭分明,但是随葬品中却有融合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的大汶口 良渚式陶器,这说明要么是大汶口人、要么是良渚人在制陶时采借了对方陶器造型的某些特质融入陶器制作当中,在陶器制作方面出现了涵化。来自良渚的人死后头向不是按良渚文化葬俗朝南而是按照大汶口文化葬俗朝东,良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