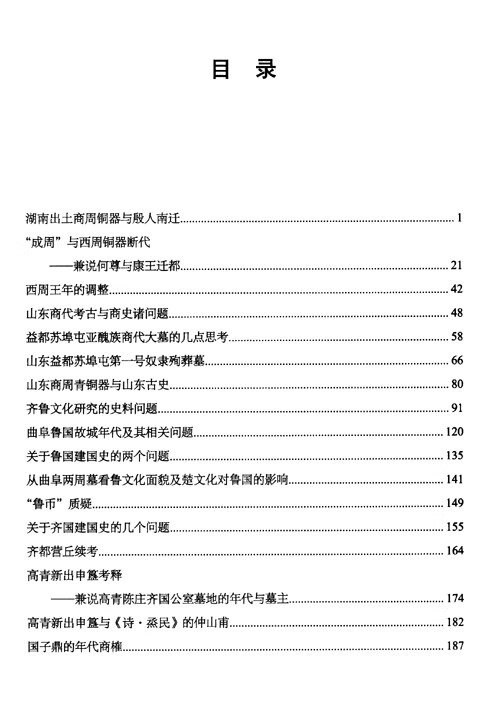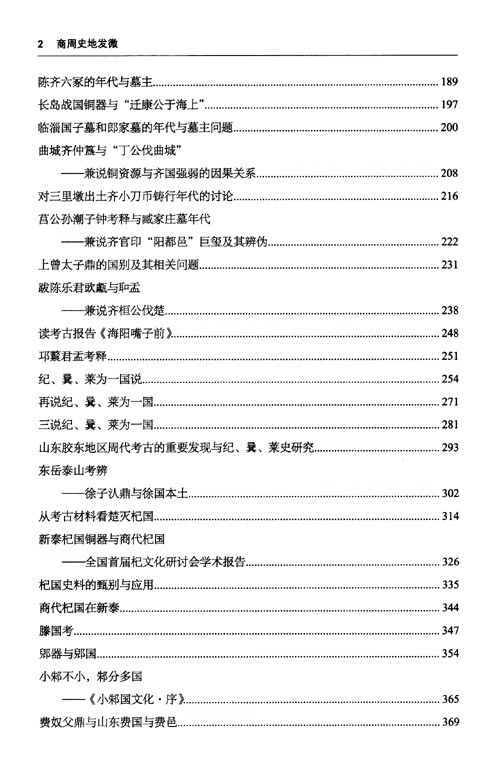阎、惠先把《毕命》判为伪书,而后认为《毕命》的记时“古今文皆无”,或认为“梅赜袭其词”。这样的论证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何况16字中还有《毕命豐刑》和“王命作册豐刑”两种不同的说法。顾名思义《毕命》应是册命,而《豐刑》则应是刑法之类。《毕命豐刑》应是把性质不同的两篇著作撮合在一起。阎辨《毕命》此条,并没有搞清《毕命》与《豐刑》的关系,而且充满疑似之词,用连自己都没能搞清的材料来否定《毕命》,显然不足为据。其实,无论是《毕命》,还是刘歆所引的《毕命豐刑》,其记时中的“庚午朏”,都是后人所追加。因为相当于月出的“朏”,在西周金文中一律使用“生霸”,而绝不用“朏”。阎、惠还列举《毕命》中与后世经籍中相同或相似的语句作为《毕命》作伪的“赃证”。其中如“左右先王”“殷顽民”“升降”之类,都是古代的习惯用语,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至于“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与书序“分居里成周郊”语句相似,并不能证明《毕命》抄书序。更有甚者,惠栋居然两度引用《汲郡古文》的材料作为《毕命》伪书之证。所谓《汲郡古文》,其实均出自《今本竹书纪年》而不见于古本。《四库总目·竹书纪年提要》和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曾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已成定谳。用伪书辨伪,指控《毕命》系伪书,当然不能视为定论。确认伪书的抄袭,必须列举确凿证据。如前人揭发《管子·大匡》抄袭《左传》而不知删除记时的“二月”“五月”“九年”。a又如我们曾指出《管子·势篇》中“天时不作,勿为客”“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圣人因天”“逆节萌生,天地未形”“成熟之道,嬴缩为宝”等大量与《国语·越语下》雷同的语句是抄自《越语》,因为这些语句都是来源于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对话。每一次谈话都有其时代背景,都是针对吴越16年间政治、经济形势而发表的议论,是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所采取的对策。而《管子·势篇》抽去了时代背景,杂乱无章地抄袭上述语句,让人感到唐突费解,不知所云,必伪无疑。a阎、惠虽然罗列出《毕命》与后世经籍中相同相似的语句,但却未能列举出《毕命》抄袭的证据,伪书说似难成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把《毕命》排除在外未必妥当。恰恰相反,《毕命》中对康王时称“成周”而述周公事称“洛邑”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必有其根据,是后人无法拟作的。尽管其中羼有后人所加的记时和“四夷左袵”之类似为晚出的语句,但不能全部否定其史料价值。
综上所证,何尊应是康王五年作器,“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应是康王迁都于成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