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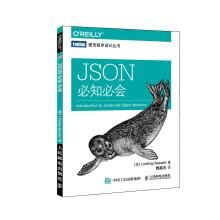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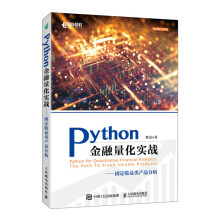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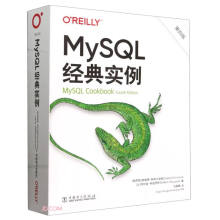
(1)作为清朝统治者所力推的松花石砚,为何没有在有清一代达到端、歙的高度?受到皇帝赏赐的松花石砚,本该是一项荣誉,但在受赏者的笔下却鲜有痕迹留存?
(2)下洞开采原料的石工,在砚石品级的判定上,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反而是砚石成品的使用者——文人精英,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石工丰富的实践经验难以诉诸文字,从而阻碍了相关知识的传播,文人书写的便利性使其在砚石的评价中占据了制高点,甚至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性,文人撰写的文本中不乏对石工的贬低之语。
(3)作为清初最有名的女性制砚家,顾二娘从众多男性匠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流传后世的“顾大家”。矛盾的是,这样一位“大家”的生平事迹,却缺少专门的文字记载,只能在记载其他相关人士的字里行间去找寻,甚至其流传后世的名号,也是被冠以夫家之姓。
(1)配图I.1
康熙帝在扫除构成清朝正统性最大威胁的节骨眼上,重申每日亲临“文墨”,并征求隐世良才,无疑展现出战胜者试图和解的姿态。一方坚石的用途,从砥砺磨刀到磨墨,代表治国方略从武治向文治的转变。约十年后,当皇帝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三度东巡以告祭祖陵期间,在行围狩猎、捕鱼时发现更多适合制砚的砥石,包括在乌拉山(今吉林省境内)寻获一块绿石。他或许也曾命人在这些石矿附近进行系统开采。在皇帝和匠人上下合作,致力于采集原料和制作的同时,一种崭新的清宫文物就此诞生。
不出十年,康熙帝开始将松花石砚作为礼物,赏赐内阁翰林官员。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早朝,他在内殿南书房召见60名翰林学士,每人各赏赐松花石砚一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造办处增设砚作监造二人,并将其移入养心殿,很可能是为应对赏赐砚台带来需求增长的一项措施。7 连同御赐书籍和御笔书法在内,赏赐砚台是向汉人受赐者明确传达一个讯息:我们在文化认同上,价值是一致的。康熙对汉族士人文化的尊崇虽不乏政治动机,却无疑是出自真心。即便如此,实际上,从原则到实践层面,清帝国对文物制作的管理和态度皆与前代大相径庭。
(2)配图2.5
伍丁先师诞供奉神牌所勒刻的文字,用的是全国通用的官僚化话语,端州砚工的土地神以及用黄岗话念诵的咒语和行话,则让我们管窥仅限于砚坑流传的地方知识。在最珍贵的老坑洞口,砚工立起一块石碑,阴刻三行字。中间一行“洞口之神”字体最大,将石碑转化为一位守护神,左右两行较小的字则表达了石工渴望得到洞察力和神力:“一见能通晓”“举手活如龙”。21(图2.5)“通晓”在粤语表达中是指出于瞬间和本能性的领悟力。矿工进入洞口前,要焚香祭鬼神,鱼贯经过石碑进洞,每个都要说:“唔该(请)谢一谢(让一让);我哋来开工啦!”
(3)配图3
随着顾二娘崭露头角,她的不同称呼在不同主顾中逐渐传开。这些名字为观察这一位异乎寻常的女琢砚家在时人中引起的反应,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一端,如黄中坚,称她为“顾家妇”,展示了一种儒家正统性别观:妇女应以夫家为最终依归,以后者利益为先。事实上,正是这种使命感令顾氏制砚变得无可指摘;在中国商业史上,家业继承除与男性血统相捆绑外,亦屡有无子嗣的遗孀为妇德而承担夫家事业之美谈。
与此同时,另一个苏州作者朱象贤,捎带讥诮口吻地提及顾氏原姓邹,养子是过继给自己的侄子。在儒家教条中,已嫁女子不应与娘家有任何纽带关系。朱氏暗示着一个妇女或可同时回报娘家和夫家,留下重新想象顾氏职涯的一个空间—其制砚事业或不能完全由传统妇德出发去理解。
(4)
厘定真迹或赝品的鉴定过程,虽然有助于产生新知,但是最终易于导致忽视顾二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重要面向:她从一个地方手工艺人向一个超品牌的演变。对一组传世砚台展开分析,并对照文献,能让我们厘清这个转变过程。
使用“超品牌”(super-brand)这个词不仅是指超级名牌,更因它犹如刘禾笔下“超符号”(super-sign)那样的功能。一个超品牌通常不是指一种独立风格,而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14寻找真的顾氏砚,话是没错,但方向有误,易使人一头钻进死胡同。寻找真迹需要逆推过程直指其源头(制作者之手或作坊),而将顾氏定位为超品牌,需要将目光从单一源头延伸到所有相传是由她制作的作品。研究者的最终目标不是去定夺每一方砚的真伪,而是设法了解为什么某一类砚在某时空会被人觉得是可信的?
从18世纪早期至今日,艺术市场顺应供求而出现顾氏砚,即便它们是赝品—实际上,尤其是赝品—也是文化环境的风向标。论及顾氏的文献(不管正确与否)以刻本和稿本形式流通,伴随着顾氏砚之买卖、馈赠和收藏,引发追逐顾二娘的热潮,至今未见衰退。随着时间推移,文献和砚台两种媒材掺杂愈来愈多想象成分。要追溯这个符号意义网,需观照产生两类材料的特定地点,考虑到知识、图样、感情横跨媒材和地域的传播方式。
(5)
当“藏砚家”的文化形象在北宋开始成型时,米芾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要成为大藏家一般都要有癖,而这位我行我素的艺术家留下了大量奇闻逸事,可供后人传颂、膜拜。传闻宋徽宗曾传召米芾在御前赋诗,书写于一屏风上。展现了大师级表演后,他抢过皇上的御砚,不顾上余残墨,抱在衣间。米芾认为此砚经他濡染,已不再适合御用,希望皇帝能赐给他。徽宗最后答应了。在另一则记闻中,一个友人将这个把戏反施于米芾身上,在米氏新获的宝砚中和以唾沫来研墨,强迫对方将那枚砚送给自己。
爱砚者的讨要把戏推到极端,便演变成贪官无止境的索求贿赂以及对名砚的巧取豪夺。与此相反的是,自律的官员连百姓相赠的一枚砚都不会收,如北宋以清廉著称的包青天包拯(999—1062)。这些故事清楚表明,砚不再只是书房用具那么简单了;一方上佳砚台的价格远大于其砚材和书写价值。例如,米芾曾通过两位有权势朋友的搭桥牵线,用南唐后主李煜(961—975在位)旧藏的一座大砚山,换取位于江苏丹阳北固山的一片土地,在那里筑书斋。
不合时宜的慢书 / I
致 谢 / VII
导 言 / 1
第一章 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 / 15
新技术官僚文化 / 18
陶人之心:唐英和沈廷正 / 22
康熙朝宫廷的设计大师:刘源 / 26
刘源的跨媒材龙纹 / 31
“内廷恭造之式” / 42
雍正对造办处的改造 / 46
工匠和皇帝:内廷样式的缔造者 / 49
雍正治下的砚作 / 53
宫廷和地方之间:帝国宣传的局限 / 60
第二章 肇庆黄岗:砚工 / 65
灵砚和书写 / 69
采石的工具 / 70
工匠的识字问题 / 74
勘探和采石的专门知识 / 78
士人:石工知识在北宋的文本化 / 83
米芾:打造权威的鉴赏家 / 86
清代考据学:外省目击者重来端州 / 91
本土专家的自我展现 / 99
重访石工 / 104
第三章 苏州:女工匠 / 107
专诸巷 / 109
顾家父子 / 112
出师 / 116
作品群组 / 121
定制过程 / 123
技艺等级 / 126
镌字 / 129
款识 / 133
杨氏兄弟 / 141
董沧门 / 146
造访顾二娘 / 152
第四章 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 / 159
杏花春燕图 / 160
地点、媒材和超品牌 / 168
顾二娘典型砚样 / 177
富立体感的砚 / 181
王岫君的文人山水 / 185
量产的菌砚样 / 193
铭文格套 / 195
从超品牌到神话 / 198
女性在父系家谱上的缺席 / 200
顾二娘与清初制砚之革新 / 202
第五章 福州:藏砚家 / 205
福州藏砚圈与《砚史》 / 208
藏砚在宋代的起源 / 214
玩砚与士人男性特质 / 219
建立一批收藏:家传 / 224
市场中的实用专业知识 / 230
现代性和新奇性 / 235
赠砚 / 241
无形的传家宝 / 250
结语:文匠精神 / 255
实践文匠精神 / 258
金农和高凤翰 / 261
从士大夫到工匠型学者 / 267
文匠的性别问题 / 271
附录1 清初文献记载的顾氏砚总录 / 275
一、大致年代确定者 / 275
二、年代不详者 / 279
附录2 各大博物馆藏带顾二娘款砚 / 281
附录3 福州赏砚圈成员 / 285
附录4 林涪云编辑《砚史》的版本史 / 289
参考文献 / 295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 319
译者后记 / 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