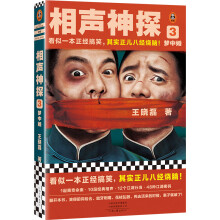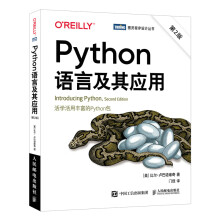导论
器物的造型与生活方式相连,器物的纹样与人的思想意识有关。汉唐文物中出现了角杯、长杯、高足杯、带把杯等不符合中国生活习俗的器物,而一些器物上的怪兽、人面、裸体等装饰也不见于中国的传统纹样。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器物和特殊纹样?它们是用于现实生活中日常使用?还是作为珍贵物品被收藏?另外,塑像、图像中那些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人来自何方?有些图像中奇异的内容究竟表现的是什么?
如果说关于史前出土的一些遗物是否与外来文化相关还似是而非,那么汉代以后出土的遗物则不必再去怀疑了。扩大视野去比较观察那些似乎无固定模式、自由随意创作的器物,会发现它们原来竟与外来文化有关。风格独树一帜、带有异邦情调的器物受到欢迎喜爱,反映了人们的特殊心理,与其说属于物质世界,不如说属于精神世界。然而,一件遗物经历漫长的岁月被发现,所包含的信息会被隐藏或消失,好在考古出土的器物等,常与遗迹、环境以及其他遗物共存,组合关系仍部分地构筑了历史现场和故事。
对于考古地下出土的一些奇异的文物带来的惊喜和疑惑,*初学者们共同的努力就是考证它们是否来自外国,或是否与外来文化有关。个案研究,通常致力于某种器物的来源和变化。随着外来文物的发现增多,被破解的疑惑也越来越多,认识外来文化的窗口被逐一打开。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量个案逐渐构成的轮廓框架,日常生活的琐琐碎碎,一点一滴地为整个文化面貌建立起一幅合情合理的全景画卷,提供了进行整体解读的可能。从学术自身发展上看,由考证“是什么”转移到“为什么”的探索是必然的趋势。把看似无关的零散遗物在“外来文化”的框架中做一次整合,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还会发现历史上各种文化都是通过不断地接触,在交流互动中发展。用形象揭示文化的交融更为鲜明直接,由此引申到阐述外来器物与中国文化这一层面的探索更是十分必要。
选择外来器物为研究对象,并进入对古代文化交流的思考时,会想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早期政治地理概念,以及被孔子发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大一统观。这种观念在人们无法跨越那些令人生畏的地理障碍时,消极地影响限制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战国中期成书的《禹贡》将中国分为“九州”,包括了黄河及长江流域。另一部先秦古籍《山海经》以中山为中心,四周有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这一牢固的以我为中心的观念发生动摇,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张骞凿空”事件。“张骞凿空”的直接原因是汉朝要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历经千辛万苦的旅行却成为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突破。意外的收获是,当汉武帝仔细聆听了张骞的所见所闻后,开始制定了沟通欧亚之间交往的宏图伟略,从而开创了中、西方之间官方的正式往来。接下来班超父子的西域经营,不再是纯粹的政治军事目的,庞大的使团常常带着贵重的礼品,往来于各地,呈现出具有浓厚友好交往和商品贸易的特色。此后在各国互派使者的常态中,一代代肩负重任的使者、探险家、僧侣穿梭于异常艰难的戈壁沙漠,寻找着东西方文明对峙中的调解办法。即便在中国割据王朝林立、政权交替时,也没有阻挡中西双方的往来,战乱与混乱又提供了别样的文化互动的方式。延续到唐代,人们潜意识中把异态文明看作是自身的敌人、并采用一些极端方式加以对付的做法得到改变,对异态文明满腹狐疑的心理被求知和贸易的渴望取代。中国古代帝王和官修史籍的编撰者虽然都认为自己统治着世界,周边邻国为“蛮夷”,在交往中他们合乎情理地要朝献,从而获得赏赐。到了唐代,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纯粹的商业行为远远超出“朝贡”与“赏赐”的特殊商贸关系,人们也不再一味用至高无上的心态来描述其他诸国,某些近乎诋毁的语言也大大减少。当人们的视野开阔后,似乎得出了有差异才有交流的必要共识,对外来文化、异教有了容忍和默认,文化的交融不可避免。
1957年向达教授出版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63年薛爱华教授又出版《撒马尔罕的金桃》 。两著作通过文献学、语言学和少量实物对唐文化中的外来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今看来,在钦佩他们真知灼见的同时,又不时感到诸多的遗憾。向达教授虽极力搜寻实物证据,可惜当时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刚刚开始,材料远不丰富。薛爱华教授查找出唐代的外来物品有18类,170余种,绝大部分只见于文字中,即使带有具体描述,也难以在那含糊、夸张甚至神化的文字中体会外来物品的真实样式。由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和考古发现不甚相同,而唐代文字描述外来事物的高峰时期比考古出土的大量实物的发现时代又几乎晚了整整两个世纪。文字未必都是现实世界的写照,很多是通过怀旧情绪诉说着早些时候的繁荣。考古文物的直观性和时代准确性,为研究唐文化中的外来影响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文献记录宛如云烟飘渺,实物发现却是真实鲜活。有幸考古这个新学科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飞速发展,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迹、遗物纷纷出土,促使人们不得不在新的条件和时代高度上再次认真考虑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这一命题,而且不再需要纸上谈兵,实物标本就带来诸多新的启示。本书是在笔者二十多年来发表的几十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作的,是对中国古代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器物、图像等进行的研究,以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为基础,材质有金银、玻璃、陶瓷、陶俑、壁画、雕刻等,遗迹涉及沉船、窖藏、墓葬,地域包括中国及东南亚、中西亚。全书以丝绸之路为宏观背景,以零散发现的个体文物为切入点,目标是探索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互动。
外来器物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个大问题,但不是空洞的宏观理论,用实物研究历史,少不了一些繁琐的考证,本书的六个章节,便是从材料出发设定的。
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的石刻图像展示了中亚、西亚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曾引起国内外学者发表诸多看法。本书第一章首先探讨了如何对这些墓葬、图像内容给予定性,遗迹整体属于哪种文化系统,怎样用图像阐释历史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如被泛称为“狩猎”的图像,应分为“捕杀”和“搏斗”两类。“捕杀”图中人物居主导地位,追捕逃窜的动物。“搏斗”图中人与兽不分主次,双方都在攻击。前者称为狩猎问题不大,后者如果也称之为狩猎则是被误解了。“搏斗”图像直接渊源于波斯、粟特。图像中人物骑象、骑骆驼与狮子、野猪激烈争斗的场面并非粟特或波斯人现实生活的场景,而是表述信仰中的理想家园。三座墓的图像中,有很多胡瓶与人物共存在生活场面中,参照考古发现的实物胡瓶,可以看到胡瓶在中国早期传统的生活器皿中没有出现,而是在北朝出现,唐代盛行。第一章也会讨论胡瓶的传入与流变,以及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器物制造甚至生活方式。
考古出土的俑类中,胡人与骆驼、马、货物的搭配,像特写镜头的再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为什么会出现胡人俑?他们象征的身份是什么?本书第二章根据胡人出土时的位置、装束、组合,将其分归为驯马(驼)师、商人、狩猎者、军人、侍从、艺术家等,对文献中屡见不鲜的“胡旋女”“胡姬”,也从考古发现的俑中考辨出来。汉唐时期突然涌现、细致刻画、特别偏爱的胡人及驮载丝绸、器物的骆驼,并出现格套化的组合,可视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述说着在一个宽容的文化氛围内,西方各国、各族人沿着沙漠、戈壁、草原来到中国的情景。
玻璃对古人来说充满神秘感,产生出很多传奇与神话,其中重要的就是与远方异国相关。本书第三章考证南京市富贵山东晋墓的玻璃碗,应是罗马统治区域内的产品。陕西咸阳北周墓的玻璃碗和西安东郊清禅寺的玻璃瓶是萨珊器物。讨论唐代玻璃时认为,当时的“琉璃”就是玻璃。唐朝人在解释玻璃时有特别的角度,经常与异域文化联系在一起。西方玻璃不仅传入中国,还同中国制造的玻璃一同东传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本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认为8世纪中叶开始“丝绸之路”绿洲路主干线衰落,晚唐、宋、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很可能是通过北方草原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获得,伊斯兰玻璃传到中国,使中国几起几落的玻璃制造终于得到缓慢的发展。
举世瞩目的何家村遗宝中有些奇异的器物究竟是输入品?还是仿制品?各类外来器物为什么会聚集在一起?本书第四章讨论了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日本银质“和同开珎”、萨珊凸纹玻璃杯等。又通过对何家村遗宝中七件独特的金银带把杯的年代、分组讨论,发现了唐代器物由输入、模仿到创新的演变过程,指出官府作坊中应该有来自粟特的工匠。此外,还对奇巧、新颖的玛瑙兽首杯和长杯进行了研究,指出外来器物经融合改造后,虽不易察觉出渊源所在,但从隐约留下的异域意味中,可看到唐代的艺术品位的改变。
南亚“黑石号”、井里汶沉船满载着中国的外销产品,有些在中国也未曾发现。本书第五章指出黑石号中的一枚看上去并不精美的铜镜,正是文献中屡见不鲜,实物却是首次发现的“百炼镜”或“江心镜”。三件青花瓷盘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早、*完整的青花瓷器。带“盈”字款的唐代瓷器,一般认为是邢窑产品,官员收买后要进入皇室的大盈库。黑石号带有“盈”字款的是白釉绿彩瓷,还有的刻“进奉”字款。说明“盈”“进奉”字款的器物也会流入市场。金银器中非唐代本土风格的造型、纹样的器物在海外贸易船上出现,透露出唐代扬州在制造和销售金银器时似乎有外来购买者的参与。井里汶沉船中的玻璃器,与以往研究中的有些外国玻璃可能来自海路不谋而合,若干形状不规则、呈深绿色的玻璃原料,或许就是中国文献中进口的“玻瓈母”。沉船中的八卦镜,可以推测是作法事之用镜。
韩国武宁王墓、日本高松冢古坟分别是两国划时代的考古发现,也打开了一个认识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武宁王墓与中国梁朝诸王墓在形制、花纹砖、桃形灯龛和棂窗等细节上的惊人相似,应不是一般模仿,或许有梁朝工匠、画师直接参与设计和修建。墓中出土的青瓷器、铜镜、钱币也来自中国。以武宁王墓做参照,可以从泛称的南朝墓中确定出一批梁朝墓,这对认识梁朝诸王墓葬特征起到重要作用。轰动日本的高松冢古坟壁画中有四神、人物和星象图,其墓葬壁画效仿唐墓,是中国文化外传的案例。韩国新安沉船的元代金银器无人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其中银炉、灯、净瓶成套的组合中国也未曾见过,应是寺庙货主按照订单采购的商品。参照船上浙江龙泉窑瓷器,可推测新安沉船的始发港是庆元港。
新的器类或器形的出现,或与起居生活变化有关,或与信仰有关,再就是与外来文化有关。将具体器物置于遗存整体之下,纳入时代背景之中探讨,采用细节考证与宏观讨论结合的方式,尽量与文献相互印证,可能就会发掘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因。如关注中国对外来文化哪些方面感兴趣,愿意吸收什么,哪些内容和形式能在中国长期流传等,无论哪种器物,它不仅是一种材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它们诠释着古代多彩世界中快乐的生活、奇异的发明、精妙的艺术,同时还是文化传播的媒介,述说了微妙而鲜为人知的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历史。器物的演变所透露出的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选择、过滤还是汲取,接受的状况是扬弃、改造、融合还是创新,过程中经历了反复的重组、试错。尽管有些器物演变后,外来因素渗透融合以新的面目出现,不再体现异国情调的燕婉热闹,也看不到文化变革的轰轰烈烈,但在其与西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模糊的背后,仍能看出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藏在人们心中的精神文化和表露出来的物质文化的双重改变。笔者对于外来、或与外来文化有关文物的探讨,有的是首次确认辨识,有的是首次解读,有的是首创新说。所得出的结论或许与众不同,也可能还需要完善甚至更正。但期望引起关注并更值得继续讨论的是,书中对于汉、唐文化转变的问题的探索。
人们喜欢用“汉唐盛世”来形容中国历史上这两个重要王朝,然而从物质文化或者说实物遗存上看,两个盛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之间缺乏关联性和结合性。探讨盛世转变的原因时会发现,汉代开辟了丝绸之路后,中国西南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部寒冷的西伯利亚,东部浩瀚的海洋,南部的热带丛林,已经不再是严酷的地理屏障,以往相对隔绝的地理屏障被打破。逐渐复杂多样的水陆交通网使人们四处周游的机会大大增多,国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