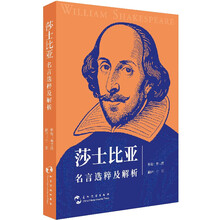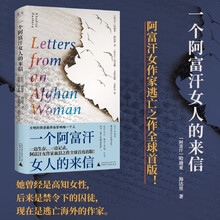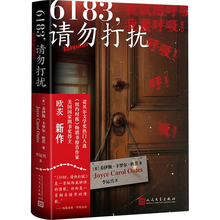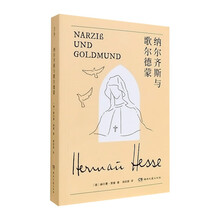《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隐蔽面》:
因此,不管精神分析者所谓全凭个人经验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必须存在于伴随大写的整体原始关系基础上,其实这种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规范。譬如,父亲的愤恨是以跟他人发生了近因的、亲历的关系为前提的。当然我不是想说孩子在与父母发生一切接触之前就已经抽象化地确定跟他人的关系。我想说孩子只能感知父亲作为建立在人类现实前本体论的理解基础上的一个人,在他身上和身外,尽管不言而喻这种理解的觉醒和现实化则是在与周围的人们全凭个人经验交流之际发生的。以为“人类实在性”存在于先,而后一下子与非“人类实在性”的东西相接触。突然出现在人间偶然的一个依存点上,在无数单个儿的客体中间,“人类实在中”自我“超越外围部分”,其突然出现的本身就构成与整体性相结合的实际关系。要么人是一块砾石,要么人是原始关系,即出现于存在中的生物,抑或所有关系的基础。这或许是某些精神分析学家想给我们的东西,但必须立即补充道:经验结构的研究不归他们管。然而,这恰恰是他们的谬误,因为此处既不涉及超验性意识,也与康德哲学的课题无关,既不关形式本源,也不是先验综合判断问题。尘世原始关系不会是感性认识的,也不会潜在地存在,更不会悬空待着,惰性飘浮着,它必须是有实际生活经验的,实际存在的,这就是说每个人类实在性必须自己创造自己,自我创新,是单个儿与整体的关系。整体存在,俗称“存在于世”是从单纯特殊偶然向全部机遇综合体的一种超越,预设根本不去理会个别幻象,除非,天际深处显圣,否则就像整体的某种具体限定。这种关系的模棱两可性来自于它不是整体与其自身的关系,而预设某种偶然的、意外的、失落在种种现象之中的实在性,进而形成自我超越去面对压得它不堪重负的整体性。因此,这既是投射于现象的无限单个性爆裂,并随之消失,为的是有个大环境能够存在,又是把“自在”洒落在同一个行为单位之中重新合拢组拼。与此同时,舍弃原始有限性作为个别的存在,后者显现于大写的整体性模糊深处。
简而言之,这种与尘世的关系既是体验我们的实在(或我们的躯体),纯粹而呆板的偶然性,又是超越这种偶然性的一种方式。因为超越躯体是体验躯体和使躯体存在的唯一方式。这种最初的“投射”,作为与实在的关系,将落实到社会实践,并且作为尘世中的依存方式,从世界观角度将被解释为我们“实在”的超越,是实际体验到的。这叫体现我们的选择。而我们通过超越选择本身品尝无法辩解的存在所包含捉摸不定的滋味。这种对待实在的态度在我们的眼里显露我们纯而又纯且不可言喻的品质,而在其他人眼里却像我们难以限定的风格。一言以蔽之,这是我们情感性的先验结构。这种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感受性充当我们所有全凭个人经验的情态基础:既然这种感受性确实建立我们与全部现实的联系,每次激动或每个情感表达感受性的同时都使感受性个性化。同样,对父辈或对自卑感的怨恨,对大家而言,都是通过跟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只有当我们的怨恨和自卑感在德国称之为Mitsein(部分实在)的基础表现出来时才使我们跟所有人接合。性欲,不管在何种外表下看待它,哪怕化成恋己癖,也只能在他人已经存在的尘世中得以表现:手淫本身先是跟别人搞的姿态,然后是跟自己搞的姿态。
然而,这种实际存在有自身的病理学。有一些“实在于尘世”的疾病,按梅洛-庞蒂的意思是说“我思故我在的疾病”(“我思”也是一种具体关系,由因及果,是由意识及自身的具体关系)。“实在于尘世”的二重性来自于机遇的存在物与整体所产生的关系。因此,关系绪多状态之中的一种换成另一种状态时,就有危险啦。尽管世人并不乐意抓住任何个别性不放,除非“不着边际”的个例,因为其周围全凭个人经验的某些争吵可能迫使他改变初衷,抑或至少原计划的内涵乘机发生裂缝或混乱。由此,“实在于尘世”是一种先验的推理,因为是综合性的关系,奠定经验,但可能变质,改变其内在结构,与后天的局部变化相关。这是个别发生的事情,当某些历史的、偶然的形势拿人的存在本身去大千世界冒险,向他揭示其本质的脆弱性或使他相信根本无法抽身。一位亲人的死亡可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死亡一劳永逸地揭示“不再存在于尘世”的可能性作为“实在于尘世”诸多特征之一。这种人类状况的揭露作为“不合常情”的事情有可能造成的变化,比单纯的性生活不健全重要得多:可能影响我们与客体的距离,影响我们对存在的直觉,甚至影响我们对自身的鉴赏力、倒转这种联系,就经验而论,增加或减少我们的不端正。
在使我们操心的情况下,即使过早的丧事迫使孤儿惋惜“香木般可爱的童年”,当孤儿压根儿驾驶不了青春的性功能时,我们大可不必全凭个人经验的情感范围内寻觅其主要功能了。孤儿最深刻的反应,我们在儿童“实在于尘世”之中找得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