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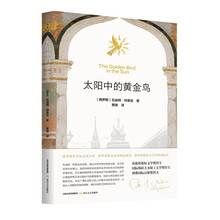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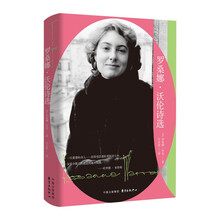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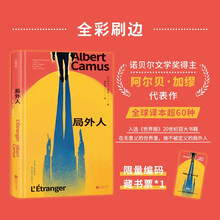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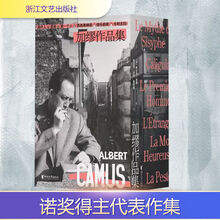


在箱子角落里,我发现了一件小小的粉色吊袜带。粉红的尼龙束腰印着小碎花。吊带上略显老气的皮筋与金属扣也一律是粉色的。腰腹部分全部镶满了细细的蕾丝,仿佛正围绕肚脐展开一场华丽的庆典。这件小小的吊袜带,形态宛如一朵花的花瓣。褪去衣物,露出女体,花瓣便会随之飘落。而这片花瓣价值一千五百日元,我咬牙买了下来,抱在胸前回了家,像炫耀宝物一样,神秘兮兮拿给母亲看。
“哎呀,这么漂亮的内衣,先收起来吧,等到正式的场合再穿。嫁人之前要把它藏好啊。这才是姑娘家该有的分寸。” 不出我所料,母亲开始了她的碎碎念。这句话是母亲对美丽内衣心怀抗拒发出的第一声非难。自那后,类似的数落又持续了十几年。我对内衣的热爱,和母亲对内衣的抵触,从这一刻起,同时埋下了种子。假若当时,母亲只是简单地赞同一句“哎呀,真漂亮,赶紧穿起来吧”,我对内衣偷偷摸摸的热爱,也许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常识光明正大地生根发芽。不过,话说回来,也一定会因为得来过于轻易,而变得无关紧要吧。说来,记得母亲总爱念叨我“为了将来好嫁人,如何如何……”,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瞧你一点规矩都不懂,将来嫁人了怎么办?” “留着将来嫁人的时候穿吧。这是姑娘家该有的分寸。你啊,总是大手大脚,啥都不知道心疼。”确实,当我还是个三岁小鬼头,对世界懵懂无知,只会挥着棍子四处乱跑的时候 ;当我好不容易在学校里获得启蒙,对万事万物生出好奇心的时候 ;当我信手涂鸦、没有心思读书的时候,母亲总要把我做的每件事都归结为一个目标—为了将来好嫁人。与其说这是旧时日本母亲皆有的习惯,倒不如说这是女性生存道路上最强有力的武器。别说过去如此,想必今天也没什么改变。我稚嫩的童心,充满了对母亲的质疑,自言自语地嘟哝道 :“那好,只要将来嫁得出去,不懂规矩也没关系咯?” 索性故意用脚去踢开障子门。年幼的我,不服气地想 :如果妈妈不唠叨嫁人之类的废话,只告诉我懂礼节守规矩,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我倒还乐意听从。孩童时期的叛逆,此刻忽然以一副吊袜带为介质,被再度唤醒。那段日子,我还未开始做内衣生意,只是一名小记者,即所谓的上班族。不过,辞职也绝非结婚之前的一段短暂假期。尽管对结婚本身并不排斥,但我脑子里堆满各种想要尝试的事,根本没有余暇也没有空间留给结婚。
从那时起,我便不断搜寻各种内衣、睡衣,渴望尝试新的穿着体验,却也次次必使母亲反感。日常之中,总交织着快乐与争吵。我从未向母亲的反感妥协。在我看来,对此事退让,便等于年轻一代向老一辈屈服。在日本,做女儿的通常都会在这种问题上做出让步。大家和母亲像闺蜜一样相处融 洽,家庭和睦,母慈子孝。我也爱母亲,却不是个孝顺女儿,否则当年怎会那般争吵不休呢?为了想穿某件红睡袍,甚至不惜大吵一架,离家出走。我这个人,在物质方面素来毫无执着,也并非执拗于 拥有那些内衣或睡袍才与母亲爆发争吵。那些年吵的架,不是对所有权的誓死捍卫,而是为了放弃的取—哪怕穿上一天再撒手,也不愿将青春收进衣橱。只希望今日纵情狂歌,明日无憾地告别。
母亲却勒令我将青春锁进衣橱。假如遵照母亲的命令去活,我的青春,何时才能自由绽放?”
每次和母亲争吵,我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新生代”的身份,以及对自由的渴求。如今想来,觉醒意识的不断累积促使我成了一名“新生代内衣设计者”。经济独立,随性而活,尽情恋爱——我开始不断向自由的生活方式延展自己的触角。世人有一种癖习,除结婚之外,还热衷把许多事情归结于某个目的。为点什么,图点什么,求点什么。
可人生偶尔做点无用之事,也无妨吧?
第一部
初出茅庐的晚报记者 / 003
抵抗、希望与热情 / 014
喂,你动真格的? / 023
流浪狗的呼唤 / 028
粉色吊袜带 / 037
TUNIC Laboratory;COCO / 051
做内衣的第三天 / 061
十六吨 / 069
生于明治时代的母亲 / 075
性感“小内内”的诞生 / 086
奥菲斯的镜子 / 096
第二部
扔出去的骰子 / 109
游戏翻盘 / 124
一坪大的工作室 / 130
茶叶罐就是保险箱 / 141
用一百乘七试试 / 157
撰写《内衣文化论》 / 173
珉珉之夜 / 185
收款与存款 / 196
男人穿起皮裤时 / 200
自信与忐忑的即兴演出 / 209
站站停车的东海道 / 217
租时间的缝纫室和太阳码头 / 223
第三部
棒球与内衣 / 237
地中海与魔女露西之旅 / 247
大人的玩具 / 257
写字间、电话、制服、锁与印章 / 262
骑驴卖内衣的姑娘 / 268
蔷薇之乡 / 288
一九〇〇年 / 297
属于大海的男人 / 306
爱琴海少年 / 321
希腊、西班牙与内衣秀 / 331
练习弗拉明戈舞 / 340
母亲与鼻吉之死 / 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