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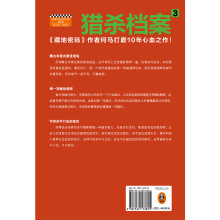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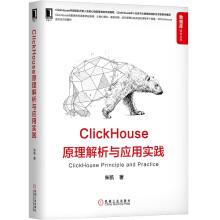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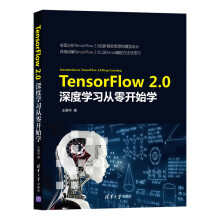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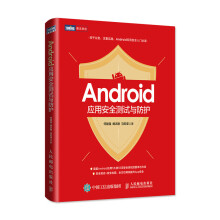
本书中所选所评的人物皆为民国时期曾活跃在文坛和教育界的不凡学人,他们虽然知名度有限,但他们与若干大人物的交往和学术论争的文学活动从不同方位及侧面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够多元化的不足,丰富了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此书稿文化探讨方向明确,资料独特翔实,对多方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状况有一定文化参考价值。
伍叔傥与胡适
伍叔傥,名俶,又名倜,浙江温州瑞安人,是胡适的学生辈。
胡适留学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伍叔傥才入校不久,是文科中国文学系一年级新生。那时候,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校园风气顿时一新。胡适扯起“文学改良”大旗,从者甚众,连一心向旧学的傅斯年也跑到他这边来了。然而,伍叔傥却不为所动,只“五体投地”地佩服刘师培。
一九一九年一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创办《新潮》杂志支持新文化运动,另几位学生薛祥绥、张煊等则以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为台柱办起《国故》反对他们。伍叔傥站在了刘师培这边,名列《国故》编辑。虽然,伍叔傥后来说:“我加入国故社与其说是‘守故’,不如说是‘依刘’。”但从此以后,伍叔傥或多或少被烙上了“国故”的印记。以至于过了三十多年后,胡适在日本碰到伍叔傥,还对他说:“叔傥,你是晚年变节。”伍叔傥正要回答,胡适马上取消了他这句,说:“不是!不是!是忠实同志。”伍叔傥接着说:“我依旧喜欢文言的。”
伍叔傥一贯喜欢文言,尤其迷恋汉魏六朝文学。
十四五岁,从乡儒周筱龄读《文选》,文思得以启发。就读浙江第十中学堂时,教师高谊先后授之《逊学斋集》《归有光集》《曾文正集》等,但只爱读《曾国藩家书》,后深喜六朝骈文和谢宣城诗即是受曾的影响。北大期间,新文学浪潮翻滚,却能“杜门玩古,物疏道亲,日诵六朝诗文,旁涉乾嘉诸老之集”。
北大毕业后,伍叔傥一直从事中文教学工作,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等校。其中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担任国文系主任长达十年,影响颇广。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朱家骅之请,曾短暂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职。伍叔傥主要教授汉魏六朝文学课程。在中央大学所授是《文选》《文心雕龙》,为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所请是专讲八代文学,在崇基学院、新亚书院所讲还是《文选》《文心雕龙》。
早年撰写的《谢朓年谱》《沈约年谱》《两汉社会风俗诗征》《八代诗中形容词副词的研究》等论文均有关汉魏六朝文学,晚年发表的《谈五言诗》亦不离汉魏六朝文学范畴。他甚至说:“中国美文,只读《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伽蓝记》《颜氏家训》足够一生欣赏。”
而且,作为诗人,他运用的创作载体主要是五言诗,这也是因为他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热爱。伍叔傥的五言诗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成就,至今还有人提到。前不久,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汪威廉的回忆文章,即以《五字今无敌》为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钟应梅以为伍诗“当代独步”并不为过。王韶生评曰:“初从小谢入手,并取法渊明、东坡两家,堪称明秀。”邓仕梁说:“诗近陶谢而饶有新意。”孙克宽认为:“雅似湘绮翁,凊劲则似三谢;颇善言情,弥尽物态,与湘翁之矞丽典重者异。”汪中撰写《六十年来之诗学》,以“后起应推暮远楼”为一篇之题,专论伍叔傥的诗学成就。适然楼主《香港诗坛点将录》,排列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四年廿年间香港诗人座次,伍叔傥列第一,尊称为“托塔天王”。
胡适晚年对伍叔傥的诗亦有评价。一日,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香港一刊物读到伍叔傥的诗,于是对胡适说:“战前我住在吴淞,有时晚上到吴淞江畔去散步。吴淞江是上海轮船出入的大港口,随时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轮船从远处驶来,江水被船头劈成两条滚滚的浪花,跟着船身前进。大的轮船过去了,船尾螺旋桨打起的波浪是很厉害的。小舢板遇到大轮船的大波浪,都用船头顶住大波浪在那里一浮一沉地挣扎。这景象,我写不出诗来。叔傥先生那首五古《海边晚眺》里有两句诗:后浪散圆纹,船头飘飞絮。这是我心中想写而写不出的诗句,所以我特别欣赏。”又说,“我常在月夜仰看空中的浮云,往往另有一种悠闲漂渺的美感。他那首七绝诗题,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其中的两句是:浮云不下廉织雨,伴月横天作画图。”胡颂平感叹伍叔傥“体物状情”的功夫很深,能写出鲜明逼人的印象。胡适说:“叔傥的诗是用力气做成的。”还问:“他的诗集印出来没有?你请他寄一本给我。”
然而,有人因为伍叔傥的研究领域和创作风格而把他看作是守旧的夫子,那实在是个误会。他的学生钱谷融回忆:伍叔傥很开明,主持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时,颇能继承蔡元培兼收并蓄的精神。中央大学国文系一向比较守旧,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入这所学府讲堂的。可伍叔傥不管这一套。聘罗根泽、孙世扬、乔大壮、朱东润、杨晦、吴组缃等来任教,邀曹禺、朱自清、老舍等开讲座。钱谷融与伍叔傥素有来往。有时,去他房间里,见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书店买书。平时与他闲谈,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
可见,伍叔傥并不排斥新文学和白话文。只不过,他反对以文言语体来分文学的新旧,曾致函钟应梅谈及:“文章体制,用之各有所适,古人之所已知,故才高者兼备众体。近如鲁迅,尚识此理,故小说则用白话,而序传墓志,亦不废雅润之音。”又在论文中阐述:“文章体制,愈后愈变,愈变愈多。愈多则用之愈得其适。要是有了那一体打倒那一体,消灭那一体,那么文学界永远只有一种体裁来使用,其余多是垃圾了。提倡的人固然非积极不调和不可,但是客观的人便要有清静的头脑去观察。中国文体有四言、五言、赋、词、曲、白话、小说,等等。每一体都有一体的特殊用场。所以每一体都有每一体不可互相翻译的名著,而且最古的文体只要有更大的文学家,一定仍旧可以产生很好很新的作品,至于世人所说的,这种体裁已经是陈腐了,不会产生好文学了,这一套恫吓的语气,一定有一天会证明其不确。”
类似的观点,从伍叔傥评论胡适诗文的文章中也可得到发现。
比如《谈五言诗》一文,讲到“文言与白话不应该截然区分开来”时,举例说:“胡适引入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汉魏六朝的白话文学,如果是我的话则会作为文言文学对待。”
再比如他在崇基学院讲课说:“有人学诗几可乱真,可是以文学理论来说这是不好的,因为成了假古董,如胡适乃是。若作诗要成家,除了集古今大成之外是要自成一家,必定要有独特之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伍叔傥对于诗的要求是苛刻的。他认为《尝试集》之类的白话诗并不成功,其“格调上较好之处已经为元曲中使用到”,“无论里面有多少出色之处,也不能说是其独创的吧”。“我对于古今文学各体,除了胡适的尝试体,认为没有成功,表示遗憾外;至于近年新兴的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都要尽量地接受,同时想下功夫去学习。觉得我们的文苑里添了新东西是嘉事。”
但这不妨碍伍叔傥对胡适创造性的认可。他在《杂言诗概论》一文指出:“近代乃有胡适,创为白话诗,多士向风,浸以成体。其诗以引用俗诗,不齐句读,为其特质。虽作品尚少,人才未多。论其卓识,实非拘墟腐儒之所能逮。我知今后诗学,必为杂言最盛之期,又将由整齐而趋于参差矣。盖诗体屡变,而杂言常为之枢纽。殆以其伸缩由人,变化可以无尽,而颇利于创造之故乎。”又在《选择高中国文教材标准的理论》一文中高度评价:“我时常这样想: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人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沈约,(二)是胡适。韩愈、姚鼐,非通人也。沈约的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理论,真巧妙。后来的近体诗词曲弹词,都由这个理论上成功的。他的理论,起初看起来是一条狭路,料不到会柳暗花明,别有天地。沈约的学说,可以说是曲径通幽,胡适简直是开马路。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同有其不朽的价值。”“要想于中国各种诗体之外,创造新体,非先从灌输外国音乐,来改造新兴的乐章入手不可的。所以《尝试集》对于中国诗学的贡献,一定不会像桃花江毛毛雨大。怎管部令禁止,社会上仍旧是流行着。”
难怪徐訏这么评价:“专攻旧文学的人与我谈谈文艺思想与文学趣味而令我敬佩的人并不多,伍叔傥先生则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
伍叔傥的人生没有像他的同学傅斯年那样和胡适有过多的交集,这和他的性情是有点关系的。正如香港一位叫容逋的作家说,凭伍叔傥的出身、学历,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当代的“名学者”,“但是,他的彻底的诗人根性、他的诗人的不凡超俗的慧眼,使他能够透视这一层层虚佞的烟幕,而独脱群流;他的一生所表现的,彻头彻尾是个诗人的真性”。
据胡颂平回忆,中央大学有四位“不通”的教授,伍叔傥是“金融不通”。他有整整一个星期,光用西瓜、花生米度日。这在抗战期间并不奇怪。但他晚年在崇基学院有较高的薪水,依旧过着十分窘迫的日子,就只能说他始终是“金融不通”了。
钱谷融说,在重庆的时候,他一日三餐都上馆子吃。有时嫌一个人吃太无趣,就邀请谈得来的学生一起吃。“倒不是嫌食堂的菜不好,而是他散漫惯了,吃包饭得遵守一定的时间,还要与许多他不一定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他受不了这些拘束,所以宁愿多花些钱上馆子里吃。这样,他可以爱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爱上哪家馆子就上哪家馆子,爱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钱谷融还记得,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伍叔傥主张把《晋书》列为教育部向大学生推荐的书目,遭到汪辟疆耻笑:“听说此书为一温州人所提,足见其陋。”但伍叔傥却毫不在意,把此事当作笑谈亲口对他转述。
伍叔傥的婚姻并不幸福。妻子余氏要离他而去,伍叔傥亲送出嫁;婚后,还关切地问余氏生活如何。
如此等等潇洒作为,在一般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真真是人如其名。
抗战结束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伍叔傥在玄武湖畔购置住宅,取斋名暮远楼,请胡适题写。“日暮途远”,多少含有无奈和凄凉的意味。
一九四九年,伍叔傥去了台湾,后流转东京、香港等地。在日本,他本来受聘于东京大学,但受到一些学生的排斥,生活过得清贫,便又收了些私人弟子,在外教授中国文学。一九五三年初,胡适访日,在东京大学文学院招待会上碰到伍叔傥,约他第二天单独见面。胡适关切地问伍叔傥,是否有意换到其他大学去教书。伍叔傥表示在外国学校教中文没有很大的兴趣。胡适说:“你要怕日本人改汉字,一个人登在这里没有什么用。改也好,不要反对他。”从这次谈了之后,伍叔傥非常佩服胡适的聪明才智:“考据小心,而神明映澈,毫无呆气,确是人才。语言之妙,真如有人夸吴清源下棋,一着顾到几十着。”对胡适的观感也因此与二十年前大不同了。
伍叔傥与胡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八年,东京大使馆。那次他们谈了对近代新文艺作家的看法,意见很相近。伍叔傥感叹:“世故深了,距离自然也不至太远。”并承认胡适很多通方之论,丝毫没有冬烘气。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伍叔傥即写了《敬悼胡适之先生》,发表在三月出版的《祖国》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十一期上。
先生负天下盛名,四十余年。死之日,几于无疾而终,以温良恭俭让的先生,死得没有什么苦痛,至少,在我感到安慰,同时有点羡慕。
所谓盖棺论定,我并不在作论。只知道胡先生是好人,是有学问的人,是一位可敬而且可爱的人。二十年前,对于文学上的歧见,最近几年来,倒渐渐接近了,虽然尚有许多不敢苟同的地方。大体上,先生无疑是先觉。
天下可死之人多着呢,为什么轮到你头上来?要是小心一点,出门随从医生,开会不要离开家,也许不至于就死。先生是国家眉目,摆在那里看看,也是要的。台北的亲友们,要负相当责任的!
先生“言满天下”,而学有专精,其高深修广,也不必妄加窥测。“文术多门,各适所好”,其雅俗佳恶,更不应妄有论列。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先生是人伦师表,不徒在于学术文章之间。大海风涛,把舵人已经没有了,真可怕极了。
虽然,伍叔傥和胡适谈不上志同道合,但对于胡适这么一位“通人”,伍叔傥无疑是由衷地敬仰和敬佩的。文章最后,伍叔傥引用《后汉书》传论中论孔融和陈寔的两段文字,六十三字,“敬吊先生”:“郑昌有言:‘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维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并俏皮地说:“先生有知,不知嫌是骈文否耳。”这恐怕是伍叔傥对胡适“晚年变节”“同志”之叹的一种小小回应吧。
伍叔傥的鲁迅印象 /1
伍叔傥与胡适 /12
吴鹭山的命运 /23
刘廷蔚:昆虫学家、诗人 /31
刘廷藩:破碎了的诗人梦 /50
黄尚英之死 /60
华五是谁 /73
“吉金乐石”谢磊明 /87
林损胡适交恶考 /108
附:我的父亲林损 /125
想起次恺 /135
寻找史美钧 /153
“失踪”的孔德 /175
“文学青年”汤增敭 /194
关注《何典》之外的钱天起 /208
王服周事迹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