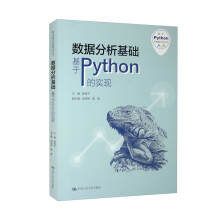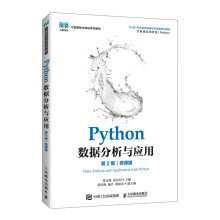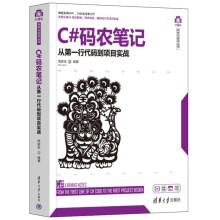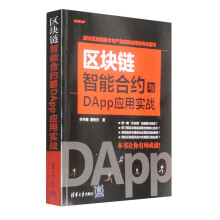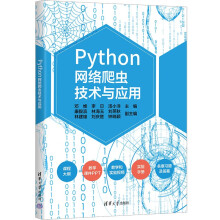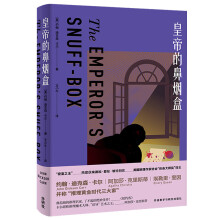《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鲁迅传》:
按说游玩是人的基本天性,鲁迅在东京之所以极少游玩,既是迫于经济压力的无奈之举,也是为了追求更高理想、理智压制天性的结果。鲁迅在弘文学院,每月只有学校发给的3元零用钱,除这3元收入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收入,只在1903年将译稿《月界旅行》“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这3元钱,鲁迅除买些廉价的樱花牌之类的香烟外,大部分买书了。那时“跑书店”是鲁迅在东京的日常功课。当时神田一带有数以百计旧书铺,号称书店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叫作“神保町书店街”。除神田外,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一带书店也很多。从弘文学院到神田或本乡,也就是3公里的距离,步行半个多小时,十分方便,因此“跑书店”也就成了鲁迅乐此不疲的事情。常和鲁迅一起跑书店的许寿裳回忆: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在“弘文”时期,鲁迅跑书店的收获很大,有社会科学著作:穆勒形式逻辑的名著《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林的《权利竞争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有历史文献:《摩西传》《西方东侵史》《世界十女杰》;有新报刊:《译书汇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还有一些日文书籍,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此外还有一本线装的《离骚》。仅1903年4月鲁迅托朋友从日本一次带回的书籍就有12种共27册。买书、读书让鲁迅获得新知,也不可避免地让鲁迅囊中羞涩。既然买书已经让鲁迅“穷落了”,他自然无法再有其他支出,毕竟出外游玩不是免费的晚餐,会有交通、吃喝等必要的花费。
除经济因素外,鲁迅身上承担着兴家、强国的重任,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对于学习之外的休闲、娱乐、游玩等则明显排斥,对他人的跳舞、游览如此,对自己的游玩更是如此。鲁迅在日本留学7年有余,除求学的所在地东京和仙台外,鲁迅只在仙台求学期间为了探访朱舜水遗迹而到过水户,此外在一个暑假和许寿裳等一起游览过箱根。除此之外,鲁迅再不曾到过日本其他的任何地方。镰仓是日本的三大古都之一,距离东京仅有5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镰仓旁边的江之岛也相当有名。鲁迅不曾到访过镰仓,也许在鲁迅的心中,“镰仓也无非是这样”。
1903年2月,浙江同乡会刊物《浙江潮》月刊在东京创刊,后来编辑部人事调整,许寿裳从第5期开始接编《浙江潮》。许寿裳向鲁迅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除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外,鲁迅还写有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铂》,此外还有翻译小说。
鲁迅的这些创作和写作都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都是有感而作。《斯巴达之魂》的创作背景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拒俄运动,为抗击俄国的侵略,当时的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准备奔赴前线。因此小说欲借斯巴达人英勇抗击波斯军队的感人事迹,来激励国人去抗击沙俄的侵略,维护国家的利益。作品叙述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的德尔摩比勒战役,斯巴达国王率领300勇士抗击数万波斯军队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一名战士因为眼病未能参战,侥幸生还。按斯巴达国法“不胜则死”,因此战士回家后,其妻以自己不是战死者之妻为耻,最后以死相谏。小说歌颂了斯巴达人“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文前鲁迅介绍自己的创作用意:“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中国地质略论》虽为科学论文,但并非只是普及科学知识之作。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纵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筑路,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引起国人强烈不满。《浙江潮》从第6期起连续发文,揭露浙江省官僚高尔伊、买办刘铁云勾结帝国主义攫取矿路权的行径,浙江留学生还在上野召开浙江同乡会,声讨盗卖矿产的罪责。《中国地质略论》即创作于护矿斗争的高潮中,意在配合护矿斗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资源。这是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中国矿产的文章,在介绍中国的地质分布、地质发育和地下矿藏的同时,把科学性和战斗性结合起来,文中指斥帝国主义派人深入我国内地暗中勘测矿藏分布状况,“幻形旅人,变相侦探”,对中国矿藏“垂涎成雨”,而那些民族败类“引盗入室”,因此我国矿藏日渐丧失,情势危急。作者正告那些侵略者:“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