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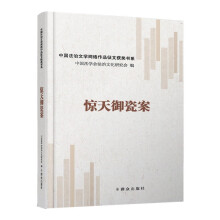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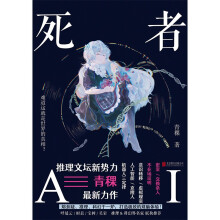



·了解莫卧儿帝国从辉煌走向陨落的全部过程,目睹它的兴起、繁荣与成就、纷争与陨落,感受古老的印度文明跨越数世纪的兴衰沧桑。
·对南印度历史的额外关注,为中国读者呈现了过去罕有了解的另一种印度,以崭新的历史视角带来更多关于印度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第一章 经受考验的民族与宗教
伊斯兰教的渗透:抵抗与接纳
拉姆德夫寺与拉姆沙·皮尔
在德里西南约600千米,靠近拉贾斯坦邦西部边界的印度大沙漠(塔尔沙漠)中,有一座叫拉姆德夫拉(Ramdevra)的村庄,位于绿洲城市贾沙梅尔(Jaisalmer)以东100千米。每年八月末九月初的雨季—或者说是当地人期待下雨的季节(即使实际降雨量很小),该村会在拉姆德夫(Ramdev)寺举办祭祀活动,以及包括祭祀活动在内为期十天的集市(mela),并因此时的热闹氛围而闻名。
巴基斯坦独立之前,信德地区的卡拉奇、特达(Thatta),旁遮普南部的木尔坦(Multan)等地的商人会来到这里交易马匹、骆驼和公牛等商品。但在今天,国界线妨碍了交流,商人、前往寺庙的朝圣者和到访集市的人群仅仅来自拉贾斯坦以及邻近诸邦。
这座村庄及寺庙的名称来自建造村庄的拉姆德夫(一说是他出生在这座村庄)。他是德里的托马拉(Tomara)王朝(印度教)末代国王阿难伽·帕拉(Anangpal,约殁于1170年)的后裔阿杰马勒(Ajmal)之子。在王族为乔汉(Chauhan)王朝(即乔哈马纳王朝,Chahamana)所灭后,阿难伽·帕拉的后裔搬到了这一带居住。阿杰马勒也是其中一员,但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子嗣。据说是神怜悯信仰虔诚的阿杰马勒,才将拉姆德夫赐给了他(1458年)。
拉姆德夫很小就因显露出圣人迹象而闻名。据说,有五位皮尔(pir,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圣人)听到这一传言后,为了证实他是否是真正的圣人,特地从麦加赶来。拉姆德夫向他们献上食物和牛奶,但他们声称忘了带自己的餐具,拒绝食用。看到他们的表现,拉姆德夫随即施展奇迹,迅速从麦加取来了他们的餐具,让他们深受震动,心服口服。
拉姆德夫长眠在这座印度教寺庙之内,在墓旁担任守墓人的婆罗门(印度的僧侣阶级)则会祝福前来参拜的人。拉姆德夫的墓旁也有其他墓,似乎是其家人和门徒的墓,而寺院内还设有大量的坟墓。一般来说印度教徒并不造墓,但据说因为拉姆德夫活埋了自己,信奉他的拉姆德夫派信徒从此开始埋葬遗体。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墓的造型和穆斯林墓的造型几乎一致,难以区别。
萨提亚·皮尔
与此相对,穆斯林并不把这座寺庙叫作拉姆德夫寺,而是用伊斯兰教圣人拉姆沙[Ramsha,又叫拉姆沙·皮尔(Ramsha Pir)]的名字称呼它。穆斯林认为这座寺庙内的拉姆德夫墓实际上是1458年将自己活埋的伊斯兰教圣人拉姆沙的墓。由此,其周围的墓便成了他的家人及门徒的墓,院内的墓也成了穆斯林的墓。1458年,对印度教徒来说是拉姆德夫诞生的年份,对穆斯林来说则是拉姆沙下葬的年份,不过两位圣人在活埋这一点上则具有共通性。
对印度教徒来说他的名字是拉姆德夫,对穆斯林来说他的名字是拉姆沙,这是一位一人分饰两角的圣人,而前面提到的寺庙祭祀,就是对他的墓地进行参拜和朝圣。圣人生前施展治疗、奇迹等事迹成为传说,得到夸饰,于是,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都出于治愈疾病和疗愈伤口、避开厄运、求子等希冀“降福”的目的来这里参拜。
这种伊斯兰教的圣人崇拜在北印度农村中通常称为“萨提亚·皮尔”(Satya Pir,意为“真正的圣人”或“绝不会说谎的圣人”崇拜)。将伊斯兰教圣人当作印度教或耆那教寺庙守护圣人来加以崇拜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印度各地,当然各地的叫法有所差别。伊斯兰教本来禁止“偶像”崇拜,不过透过穆斯林的“圣人崇拜”或“墓地崇拜”现象,也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发展状况。
伊斯兰教徒中,有被称作“苏菲”的神秘主义修行者。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他们从西亚来到印度西北,在城市及其周围建造了称作哈纳卡(khanqah)的活动中心和屋舍进行修行,并将这种活动传播到了偏僻的农村。除了对穆斯林,他们也会对印度教徒用浅显的语言宣讲对真主的信仰,全力追求与真主合一,把由此产生的奇迹归为真主的恩宠。这种观念与宣讲对神绝对皈依并期待其恩宠的印度教巴克提(Bhakti)信仰(见后文)有相通之处,而他们的活动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印度民众改信伊斯兰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穆斯林王权的务实政策
在拉贾斯坦西南部一个叫作贾洛尔(Jalor)的城市里,有一座曾由索纳加拉(Sonagara)王朝(1182—1311)掌控的巨大山堡。山堡城门巧妙地隐藏了起来,在山脚无法看到。只有爬到山腰,城门才会出现在眼前。1298年,伊斯兰教卡尔吉(Khalji)王朝(1290—1320)的苏丹阿拉丁·穆罕默德(Alauddin Muhammad)请求以这座城堡为根据地的拉吉普特(Rajput,印度的武士阶级)国王甘哈达德(Kanhadade,1292—1311年在位)允许其军队穿过领土以远征古吉拉特(Gujarat)。国王做出如下回复予以拒绝:
阁下的军队在远征途中一直掠夺村庄、俘获人口、凌辱妇女、迫害婆罗门、屠宰母牛。这是与我们印度教徒的准则(dharma)相违背的,因此,无法同意阁下的请求。
苏丹军队于是通过别的路径征服了古吉拉特。可是,在返程路上,接近甘哈达德国王的领地时,“新穆斯林”(归顺卡尔吉王朝,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士兵)部队因为战利品的分配问题发动了叛乱,其中一部分人向甘哈达德国王求救。国王立即出兵相助,夺取了苏丹军的战利品。得知情报的苏丹没有将怒气撒向甘哈达德国王,而是撒向了住在德里郊外的叛军妻儿:他当着母亲的面残杀孩子,并将女性变成奴隶。
这一幕过于惨烈,身为穆斯林的宫廷史官巴拉尼(Barani)为此谴责将军努斯拉特·汗(Nusrat Khan),声称是因为他在叛乱中失去弟弟,才抱着复仇之心怂恿苏丹做出如此残酷的事。但与此同时,他也写道:“男人们的罪让他们的妻儿偿还,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成了一个开端。”(《菲鲁兹王朝史》,Tarikh-i-Firuz Shahi)如此一来,责难的矛头指向的不是将军,而是苏丹了。
大多数叛军逃向了乔汉王朝普里特维拉贾(Prithviraj)三世的后裔所控制的伦滕波尔城(Ranthambore),但苏丹用计攻克了城池,将他们屠杀殆尽。苏丹没有对甘哈达德国王实
施惩罚。从后者此后还在苏丹宫廷侍奉这一事实来看,苏丹可能是因为他前来朝贡,就赦免了他的反叛举动。但对于身为拉吉普特、自尊心甚高的甘哈达德国王及其嫡子维拉马德(Viramade)王子来说,前往苏丹宫廷侍奉的行为本身以及在宫廷里受到的待遇,都是屈辱性的。他们拒绝在德里做人质,逃回了贾洛尔城。苏丹对甘哈达德国王的再三反叛勃然大怒,于1310年包围该城。次年,包括妇女子嗣在内,国王及王族成员、家臣全部“殉难”。
贾洛尔城陷落之年(或第二年),甘哈达德国王的弟弟马尔迪奥(Maldeo)受苏丹指派前去掌管位于该城东南200千米的庞大的奇陶尔(Chittor)要塞。这一使命本由苏丹之子希兹里·汗(Khizr Khan)负责,但由于人心未定,而索纳加拉家族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于是马尔迪奥取代他承担了这一任务,掌管此地长达七年。
关于贾洛尔之战,有人认为马尔迪奥站在苏丹一方,也有人认为他支持的是兄长甘哈达德。考虑到阿拉丁苏丹生性多疑,以行为“残忍”知名,马尔迪奥会得到任用不太可能是因为他在贾洛尔城陷落时投降了(并得到赦免),更可能是因为他早已开始为苏丹效力,攻城之时也站在苏丹一方。不过,如果真是“投降后被赦免”的话,则可以认为苏丹并非只是“残暴”之人,他也会采取政治利用的手段。顺带一提,后来的图格鲁克(Tughluq)王朝苏丹同样让马尔迪奥的嫡子掌控着奇陶尔。
一般来说,针对用武力予以反抗的印度教势力,穆斯林王权会依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使用武力将其消灭;至于俘虏,则迫使其改信伊斯兰教,并变为奴隶。但是,即使是印度教徒,如果最初就降服并宣誓臣属的话,是不会让他们改变信仰的,而是如前文所述,会确保其既有的地位和领地,并让他们为穆斯林王权统治服务。
这种务实政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711—713年阿拉伯军队对信德地区到木尔坦之间区域的征服。当时,他们已比照“有经者”(即齐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来对待当地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也就是说,异教徒在信仰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上得到保障。作为回报,他们则需要缴纳吉兹亚(jizya,人头税)。但是,即使会征收吉兹亚,也多半出于德里苏丹(国王)的一时兴起,实际上真正征收的情况很少。当然,正如后文所述,从制度上废除将俘虏变作奴隶的做法以及对吉兹亚的征收,已是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阿克巴治下的事了。
共存与自我变革的考验
人数较少的穆斯林征服集团要在印度统治占压倒性多数的非穆斯林人口并站稳脚跟,就不可能对非穆斯林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教法(Sharia)。与此同时,穆斯林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在这一过程中进行自我变革,以消除集团内部因为地域、民族不同而产生的歧视,并克服对印度穆斯林(从印度教改信伊斯兰教者)的政治、社会性歧视。于是,“信伊斯兰教者皆同胞”的伊斯兰教教理,不仅在穆斯林中,也在与压倒性多数的非穆斯林的关系中,在种姓制的应对方式上,其真正价值遭遇了试探。
与之相对,面对历史上无数次入侵以及移居的异族及其文化,印度文化用同化和吸收的方式显示了它的“宽容”。但是,这种优越感在面临空前强大的伊斯兰教扩张时,经受了巨大考验。拉吉普特军队在和被他们鄙视为蔑戾车(mleccha,夷狄)的穆斯林军队作战中节节败北,不断“殉难”。为此,印度教徒不得不开始探索新的“宽容”精神。
以贾洛尔之战为题材,后人在1455年和1704年分别创作了两部叙事诗,《甘哈达德王纪事》(Kanhadade Prabandha)和《索纳加拉家族维拉马德王子事迹》(Viramade Sonigara RiVata)。《维拉马德王子事迹》作者不详,但其主角是《甘哈达德王纪事》的主角甘哈达德王的王子维拉马德。
传说苏丹之女爱上了以英勇著称的维拉马德王子,在收到战死于贾洛尔之战的王子的头颅后自投于恒河。《维拉马德王子事迹》对这一传说加以改编,将贾洛尔之战的起因归为王子与苏丹之女的罗曼史。故事中,公主在王子自杀后,把他的头颅抱在胸前奔入火中,践行了萨蒂(Sati,殉死),以印度教徒身份在死后与王子结为夫妻。该作品原文为拉贾斯坦语,英译本收入原文和印地语译文,改题为“践行萨蒂的穆斯林公主”,副标题则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融合的历史性罗曼史”。
相较之下,更具重要性的则是原文用古拉贾斯坦语和古古吉拉特语(两者作为语言尚未分离)写成的《甘哈达德王纪事》。作者是比沙纳加尔城(Bishangarh,贾洛尔附近?)名为帕德马纳巴(Padmanabha)的婆罗门,据说他是应甘哈达德的五世孙阿卡伊拉吉(Akhairaj)之邀而着手创作的。阿卡伊拉吉统治何方领土不得而知,但索纳加拉家族已经失去了贾洛尔城,之后也未夺回该城,因此可以肯定他不是贾洛尔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