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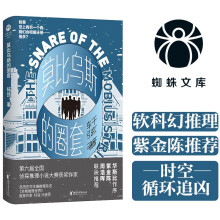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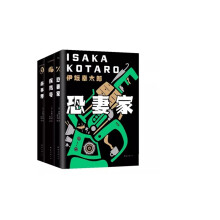


在欧洲历史,乃至整部人类军事史中,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都是一个奇迹。顺境之下其兴也勃的帝国不可计数,可逆境之下屹立不倒的帝国却寥若星辰。“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像拜占庭一样曾如此岌岌可危,却又凤凰涅槃。”恺撒与奥古斯都们的征服与荣光早已远去;这个中世纪的罗马帝国面对的是四面八方的强敌、永无止歇的围攻,以及日益萎缩的疆土、财力与兵源。然而,面对如此绝境,帝国不但幸存了下来,苦撑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而且一度迎来了中兴的曙光,最终存续长达千年之久。个中奥秘,远非“运气”二字可以总结的,何况时运往往并不站在帝国一方。本书探究的,正是拜占庭帝国的千年逆境求生史;作者迈克尔·德克博士将这套饱经试炼的战争经验法则,命名为“拜占庭兵法”。
* 宏观战略与具体战例相结合,遍采经典史料与当代史家之所长,一窥千年帝国绝境求生的战争哲学
* 知名军事史著译者马千,凭借对相关史料的熟稔与热忱,为全书额外添加了数百条细致详尽的译注条目,对中古历代帝王将相、著名战役如数家珍,堪称一份精彩纷呈的伴读材料
* 十一幅高清精细历史地图,遍览东罗马帝国山河疆域、行省军区、城市路网的千年变迁史
* 二十余幅精制战略态势图,动态解析帝国史上各场著名战役
* 附录16页地图信息翻译对照表,不但是解读地图的帮手,更是自成一部东罗马军区/地名小词典
第二章 统帅力
在其大部分历史中,拜占庭人并非以名将辈出著称——毕竟,他们也遭受了许多失利(参见第一章),他们突出的是综合统帅能力,凭此才能蒙受挫败,依旧力挽狂澜。虽然拜占庭并无与西点(West Point)类似的军校(士兵们可在此学习军事科学,汲取他人的教训),但拜占庭人和多数邻居不同,他们会记载战争科学方面的思想。帝国漫长历史中的确存在许多例外,不过指挥官常为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职业战士。考虑到所托付人力、物力的价值,他们保持了一种高水准。
当一种军事惯例、战争文化发展了超过千年,归纳它就必须谨慎小心。最基本的领导力意味着对战略、战术的领悟,以及权衡利弊得失与勇气的结合。维盖提乌斯(Vegetius,4-5世纪)的著作 或摩里士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的《战略》(Strategikon)均未详细讨论一名将领的品质,不过,书中呈现出的那些必要的学识和天性表明了除个人勇武之外,对后勤学的掌握也十分关键。对军队状态、士气的清晰把握十分重要。在利奥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皇帝《战术》一书中列举的将领特质绝大部分都不会令现代读者感到陌生。一位指挥官应当拥有自制力,庄重,清醒并且清廉。此外,他还应具备聪慧头脑,年龄适中。身体强健及耐受力也是被看重的。他必须能够赢得部下的尊重,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对当今读者而言,令人更为讶异的对其宗教虔诚与子女情况的格外要求:利奥认为拥有子女的男人更有干劲,同时也更青睐出身贵族而非寒门之人。
以上特质被认为是成为“将军” (希腊人称strategos,复数形式strategoi)或其它次级指挥官的关键。我们手中的史料很少谈及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作用,更遑论类似今日军士(NCO)或其他扮演关键角色的低阶人士了。对专业素养和军事操练的强调令战士们具备战术上的才能和灵活性,不过,下级军人似乎缺乏主动性。这里并没有拜占庭的“长征” ——一支军队失去了领袖仍能杀出血路,亦无拜占庭“士兵战役”——部队脱离指挥仍取得胜利。失去坐镇指挥的将领或皇帝往往意味着战败、溃散。这种印象部分要归于我们手中资料的性质——其作者突出了自身所属精英阶层人物的事迹与英雄气概。军队在核心层面依旧保持了专业性(虽然这一点上,黑暗时代的军区部队存在争议),因此,拜占庭军队临阵折将后无力重振旗鼓,便不能归咎于军队的组织。就中世纪而言,拜占庭的军官制度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先进性(参见第三章)。既然下级军官似乎主要依靠经验、战功来赢得晋升,那么表面上对战场危机缺乏应变恐怕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
社会影响清晰地塑造了战士们的态度与反应。人与人并不平等,一名穷苦的新兵甚或最优秀的低阶战士也无法和出身名门的将领相比。人的出身、财富、社会地位给予精英的不仅是飞黄腾达的门径,还包括生活方方面面的优越感。世人皆有角色,尽管并非所有贵族都曾实现丰功伟绩,但这种预期有助于解释,在随后失利的混乱中,为何军中低阶战士没有夺过将旗,重整溃兵,反败为胜——即使这番英雄壮举是完全可能的。诚然,部分普通士兵的确也晋升高位,但拜占庭社会依旧是高度阶级固化的。许多早期拜占庭时期的将领都来自精英阶层,到了拜占庭帝国中后期,大部分高级军官则属于盘根错节的军事贵族。当然,这样的人士不乏亮点。例如,达米安·达拉瑟诺斯(Damian Dalassenos,去世与998年)便是许多优秀并且后来子承父业的指挥官之一,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帝国官场和重臣所熟知,在获取高级指挥权方面有着近水楼台的便利。 不过,赢得皇帝宠信、维持指挥权对职务同样关键;尽管拜占庭也出现过一批拙劣的将领,其无能导致了灾难,但总体而言,在帝国存续期间,军队得到了妥善的领导。
虽然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并且正如手册和史实展现的那样,拜占庭士兵通常能够积极支援战友以及执行复杂的战场战术,但没有迹象表明拜占庭人鼓励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战争,下级军官重整军队或取代阵亡的上级指挥的情况极其罕见。帝国在其漫长历史中面对的是咄咄逼人、诡计多端的敌人。游牧的草原勇士,诸如匈人、阿瓦尔人、库曼人(Cumans)以其机动性、战术和武备挑战着这支最老练的军队。弓骑兵集攻击力、射程、机动性于一身,并且融合了古老的草原战争谋略,对拜占庭军队而言,可谓兵凶战危。拜占庭将领深谙胜负只在一线之间;一股显然已经战败的敌人可以迅速重组并对追击中陷于混乱或驻足搜刮尸体上战利品的军队发起反扑。对纪律性的强调以及遵守章程的需求令下层战士的主动性变得显然不合时宜。无论胜败,作为士兵的个人主义会妨碍部队的凝聚力,并让战友身处险境。
当我们了解了普通军人的期待,领袖及其部属的角色便更加清晰了。拜占庭人和其他前工业时代的人一样,热衷于预兆。任何努力的最终结果均归于上帝。战役不过体现了上帝的旨意:士兵死战因为职责如此,其勇武和技艺未必对战局产生决定作用。当然这有些简单化,然而,拜占庭文化中的这种宿命论在军事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指挥官可见的才能、虔诚和健康构成了军队士气的主要部分。维盖提乌斯写道,战前远离阵线的将领对军队的信心会造成重创。 917年,利奥·福卡斯无人的坐骑从阵中跑过时,军队误以为主将殒命,引发了恐慌。 大战之前往往会浮现上帝眷顾或不悦的征兆,预示了最终的战果,而将领的英勇事迹则成为重要的精神上的“标记”。623-24年间,当希拉克略在萨罗斯河 (Saros River)桥上击倒魁梧的波斯战士时,这激起了军队获胜的信念,并非因为皇帝清空了桥梁,而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大大鼓舞了部下的信心。
因此,领导力源自高层;将领被认为既为士兵们的上级,又是一名出众的战士,他还具备一层精神上的“光环”。通常,他会较绝大多数部下更精通战略、战术。基本上,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幕僚团构成了军队的神经中枢。指挥权属于那些严格执行军纪并拥有权威的将帅;在帝国历史中的战役里,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士兵们易于陷入混乱,而通讯亦不可靠(发送信号仰仗于信使、旗帜和乐器)。最优秀的军队也是笨拙的,一旦战端开启,指挥与控制几乎荡然无存。如果一名将领倒下或失去联系,既然他身边的精锐已经阵亡或逃离,指挥、控制的丧失便会很快出现。相反,在那些旷日持久的鏖战中,如果指挥官尚存,拜占庭军队也能表现出自己的韧性,例如971年的杜罗斯托鲁姆战役,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确实存在下层中缺乏领导而成事的例外,尤其是在早期。低级军官于军事危机中攫取控制权的最佳范例恐怕当属福卡斯 了,据说他只是菲利皮科斯(Philippikos)将军麾下一支塔格玛 (tagma,编制约300人)中一名卑微的百夫长 (kentarchos)。面对因欠饷、恶劣服役条件引发的兵变,菲利皮科斯无力平息士兵的怒火,逃离了军营。出身贫寒的百夫长福卡斯此刻获得了权力,被军队举在一面盾牌上拥立为帝。福卡斯率领叛军挺进君士坦丁堡,最终夺取了城市,杀死了摩里士皇帝。除了军事动乱的特殊时期,上述“以下克上”的夺权几乎是不存在的。
作战领导能力通常依靠经验积累。6世纪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 (Prokopios)记载道,许多领袖都是因为其能力从普通行伍中提拔的。但到了拜占庭帝国早期,很多指挥官都来自军事世家,它们的成员追随着成功前辈的脚步,例如后来反叛的维塔利安(Vitalian,去世于520年)的侄子约翰 ;抑或出身于为帝国服役的蛮族精英。例如格皮德王子蒙杜斯(Mundus),他在巴尔干和东部边境为查士丁尼效命,忠心耿耿。
早期(4-7世纪)
直到378年阿德里安堡的灾难发生,皇帝们常常御驾亲征。在出身低微的皇帝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戴克里先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通过行伍生涯登上了皇位。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约250-306)血统亦不高贵 ,像他那样的男人是通过军事服役而获得了机遇、荣耀以及权力。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一世与他的侄子尤利安堪称活跃的战士,能够身先士卒。进入6世纪,普通军人依然有机会获得高位。到了5、6世纪,皇帝不再亲自领兵,而将领的选择似乎更看重忠诚而非才华。不过,功绩依然是关键的考量。普罗科匹厄斯提及的许多指挥官显然家世平平,通过服役而获得了职权。皇宫又一次提供了佳话:目不识丁的农民查士丁(Justin)离开位于伊利里亚的农庄加入了军队,此后擢升为禁卫军一员,最终披上了紫袍 。
在4世纪,禁卫军(protectores)组成了处于执事长官 (magister officiorum)控制下的数量不明的军队。以上这些规模、部署未知的部队由一位伯爵 (comes)统领。多梅斯蒂奇 (domestici)如其名字的含义那样,构成了皇帝的亲卫,除此以外,也有普通的禁卫军。通常那些早年生涯证明其前途无量、忠心耿耿的人才会被选入禁卫军。提拔以资历为基础。普通禁卫军和多梅斯蒂奇都供应参谋——通常作为元帅 (magistri militum)们的副手,他们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任务,例如征兵,监管军需库,视察要塞等。皇帝通过一种效忠仪式亲自任命禁卫军,因此,他们为统治者及其统帅部所熟知。忠诚与才华兼备,难怪时常“鲤鱼跳龙门”了。瓦伦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皇帝的父亲格拉蒂安(Gratian)便曾是一位专业的摔跤手,后来被提拔成了禁卫军军官。
在6世纪,皇帝的侍卫与高级将领的家丁依旧是军官的重要“温床”。利奥一世皇帝(457-74年在位)组建的为数300的禁卫军(Excubitors),因其忠诚、抱负与战力而输出了许多军官。“部曲军”(Boukellarioi,得名于他们所食用的面包)构成了地方官与豪强的私人卫队。一旦527年查士丁尼登基为帝,他担任元帅(520-27年间)时的私兵被提拔进入统帅部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包括贝利撒留(Belisarios)和西塔斯 (Sittas)。查士丁尼继位时创建了一支亚美尼亚人执掌的新军,让西塔斯担任其统帅。在历经一段漫长、辉煌而又忠心耿耿的军旅生涯后,539年西塔斯于亚美尼亚一场战役中阵亡。
西塔斯的战友贝利撒留在查士丁尼掌权后同样异军突起。至529年,贝利撒留已官至东部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其地位允许他招募7000部曲;这位名将本人负责军饷和维护。其中一些是证明自己为堪用战士的普通本地人。部曲常常被派去统领正规军的分遣队或执行特殊任务,像贝利撒留这样的领袖对他们颇为倚重。在他的非洲战役期间(533-34年),派出了一位名叫戴奥吉尼斯(Diogenes)的亲兵与另外22名部曲来到汪达尔人首都迦太基城外侦查。汪达尔人奇袭了这支部队,几乎将其摧毁,戴奥吉尼斯也负了伤。549年,当贝利撒留准备离开意大利时,他留下戴奥吉尼斯执掌罗马城的3000守军。
尽管不如帝国早期那么普遍,有时罗马贵族也能获得指挥权(但很少赋予经验匮乏之人)。502-06年波斯战争的爆发令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皇帝猝不及防,他派出了四位将领,其中包括自己的外甥海帕提乌斯(Hypatios)。后者显然在490年代镇压伊苏利亚高地叛乱中汲取了战争经验,然而他缺乏谋略和勇气,最终令失望的皇帝于503年将其撤换、召回。
除了本国子弟以外,罗马人也仰仗蛮族血统的军官。帝国四周散布着尚武的“邻居”,他们提供了募兵的“沃土”,不仅是普通战士,也包括其统帅。4至7世纪,拥有日耳曼、亚美尼亚、波斯血统的指挥官是很普遍的。蒙杜斯(Mundus)是一位格皮德人(居住于伊利里肯行省的日耳曼部落)国王之子,另一位国王之侄。在520年代后期他加入罗马军队服役,并成为伊利里肯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表现卓越。531年,罗马人于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 溃败后,蒙杜斯接替了贝利撒留东部大元帅的职位。
黑暗时代,中期与后期(8-15世纪)
希拉克略复兴了皇帝御驾亲征的惯例。尽管并非全部,但他的许多继任者都将亲帅大军进入战场。在阿拉伯入侵的危机之后,军人控制了王座,皇帝亲征可谓司空见惯。高级军官多来自构成皇帝卫队的剑士(spatharii)。利奥三世(717-41年在位)皇帝曾为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麾下的剑士。国家要求领导人知兵、掌军。711年,希拉克略王朝末代皇帝查士丁尼二世(685-95,705-11两度在位)被一位军区统帅、亚美尼亚人菲利皮科斯·巴尔达尼斯发起的军事政变所推翻。狄奥斐卢斯(828-42年在位) 在安森战役中和自己的军队陷入了包围,勉强逃出生天。而在863年,米海尔三世皇帝领兵进入安纳托利亚以拦截梅利泰内埃米尔的突袭。
这种“军人皇帝”于10世纪迎来了它的顶峰——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与约翰·齐米斯基斯(John Tzimiskes)亲自领军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勾勒出一幅帝王勇武凯旋的图景。到了巴西尔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统治时期,军事精英对权势的攫取令年轻的皇帝忍无可忍,以至于他不仅通过两场残酷、毁灭性的内战剪断其掌控,还将自己塑造为理想化的替代品——英勇无畏、上帝眷顾、无往不胜的“军人皇帝”。巴西尔统治期间,他便时常在老练将领的庇护下亲自从军。
巴西尔之后的皇帝们渐渐远离了军营,直到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1068-71年在位)统治时期,他在曼齐刻尔特被俘受辱并没有终结继任者们身先士卒。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年在位)作为一名篡位者,亲自领兵,尽管也遭遇过几次败仗,但他在战场获得的功绩依然是辉煌的。其孙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依旧追随着父辈的脚步,直到此时,拜占庭伟大军人皇帝的时代才告一段落。虽然巴列奥略王朝(Palaiologan dynasty)时期,皇帝越来越少领军出征,军队规模日益萎缩,直至这一传统消亡,但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1259-82)在1280-82年以50多岁的暮年依旧领军深入小亚细亚对抗突厥人。
拜占庭帝国中后期的高级指挥官几乎总是豪门出身。9至11世纪是伟大的安纳托利亚军事贵族的时代。在最高阶将领中也有几位突出的异邦人,包括将领、皇帝约翰·齐米斯基斯(其家族具有亚美尼亚血统)以及生于亚美尼亚的梅利亚斯 (Melias)。来自皇后赛奥法诺 (Theophano,狄奥斐卢斯之妻)家族的将领也是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或库尔德人)塞奥福波斯(Theophobos)在狄奥斐卢斯麾下效力,罗塞尔·德·巴约勒(去世于1078年)是诺曼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罗马将军塔第吉欧斯(Tatikios)反而是个突厥人。不过,公元9至10世纪帝国复兴的全盛期间,大部分高级将领为本土“罗马人”(尽管其中许多是移民的后裔)。诸如阿吉罗伊(Argyroi)、福卡斯、斯科莱鲁、马勒诺伊、祖卡斯、第欧根尼这样的家族在安纳托利亚拥有地产,他们从收复此前三百年来陷于穆斯林之手的大片领土中直接获益。以上安纳托利亚家族孕育出了帝国史上最优秀干练的一批将领,尤其是巴达斯·福卡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斯基斯和乔治·马尼亚克。最终,他们攫取皇权的野心导致其失势以及面临突厥人进犯东部防御的陨落。
在帝国中期,高阶军官常常亲自参战。在一场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I)皇帝激励部将作战的宴会后,其中一员萨克提基奥斯 (Saktikios)在拂晓对扎营于君士坦丁堡外的保加尔人发动了突袭,后来殉国。 921年,保加尔人围攻阿德里安堡期间,守军主将利奥因其鲁莽地亲身出击而获得了“愚人”的绰号。 安纳托利亚将领时常与穆斯林交手;953年,巴达斯·福卡斯(约878-968年)在马拉什(Marash)附近战败后,被赛义夫·道莱 (Sayf al-Dawla)的军队围困,还负了伤。 在枪林弹雨令指挥官退居二线的工业战争之前,战争的个人特质与将领的勇武于拜占庭帝国可谓随处可见。
随着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帝国的分裂,军队的指挥权仍然由皇帝与贵族将领掌握。像米海尔八世这样的代表躬先士卒,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战术、战略才华。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JohnVI Kantakouzenos,1347-54年在位)的生涯表明,站在意识形态角度,皇帝必须积极抵抗土耳其人。约翰本人是一位称职的军官,不过,在他之后,由于帝国每况愈下,“军人皇帝”的重要性也日益削弱了。
传记
拜占庭帝国将星闪耀,不过,其中多数现代世界鲜有耳闻。他们均显露出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的才能,并呈现了那些东罗马领袖们看重的关键品质:处变不惊,谨慎对敌,深谙战略、战术、作战与后勤。与周边社会领袖更为笨拙的谋略相比,拜占庭将领更像外科医生而非屠夫,他们精于权衡利弊,掌控军队如同鸣奏乐器般优雅细腻。
图表 …002
引言 …001
第一章 历史综述 …005
第二章 统帅力 …059
第三章 组织、招募和训练 …093
第四章 装备与后勤 …129
第五章 战略与战术 …170
第六章 拜占庭的敌人 …208
第七章 战争中的拜占庭军队 …229
第八章 拜占庭兵法 …273
原注 …295
参考书目 …320
地图信息英汉对照表 …330
地图表
1. 巴尔干半岛
2. 东部边境,4-7世纪
3. 6世纪的帝国与地方军队
4. 罗马的沙漠边境
5. 688年与900年前后的诸军区
6. 780年前后的帝国
7. 1025年前后的诸军区
8. 科穆宁时代的帝国
9. 中世纪意大利与巴尔干
10. 1218年前后的继承国家
11. 安纳托利亚道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