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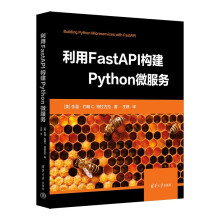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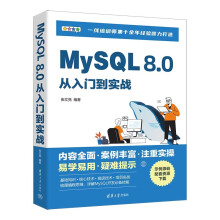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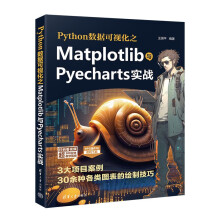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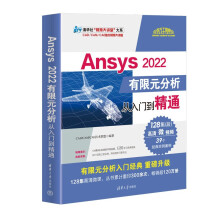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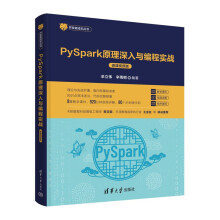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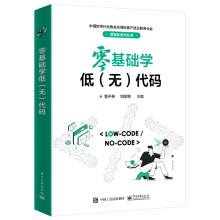
◎有美食,有风俗,有历史,有现实,一本了解伯利恒。◎从古代讲到今天,最原汁原味、最有力的伯利恒指南。◎从遗迹和故事切入,融合了历史与个人回忆、考古以及对人类和地理景观的精彩讲解。
英国人与伯利恒: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清晨,伯利恒老城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刻。女学生穿上长罩衫,背起背包,匆忙赶到修道院学校。店主们把覆盖住店面的沉重的绿松石色金属百叶窗折回去,准备营业。集市上的商人使出浑身力气推着载满马铃薯和西红柿的手推车到山上的露天剧场。晨祷结束后不久,可以看到穿着短袜和耶稣凉鞋的僧侣和修女在大理石街道上转悠。街上有卖早餐的,一辆漆得很亮的蓝色小推车上在卖土耳其面包圈,甜面包圈上撒了芝麻。一个穿着奥斯曼服装、背上绑着一个大铜壶的咖啡小贩在卖单杯的豆蔻味咖啡,只见他飞快地一弯腰,咖啡便从肩膀上方的壶嘴流出,注满了一只杯子。伯利恒最不同寻常的设施之一当数位于露天市场边缘的公用烤炉,就在镇上比较穷的那半边的五金商店那里。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的门口,人一到那里就能感到热浪袭来。烤炉有一个铸铁门,镶在砖墙表面上,烤炉里有一堆橄榄树柴。炉体的大部分被直接挖进山坡的内部,烤东西的师傅用一根长桨把炖锅推进炉膛或勾出来。四邻的妇女预定了当晚的炖菜,也把前一天的铁锅还回来。她们还将自己准备要做的饭菜和当天的菜单一并带来。公用的烤炉不仅给生活带来便利,而且还让你在酷夏之时不必再用自家的烤炉。
巴勒斯坦家常菜的主打是形式多样的炖菜,里面泡着在平底锅里稍微烘烤过、再煮过的蒸粗麦粉、薄饼。巴勒斯坦炖菜里往往放的肉比较少,主要都是些蔬菜,但有一次我吃的炖菜很丰盛,是用几只在迁徙途中路过巴勒斯坦上空的飞禽炖的。莱拉还记得一个小故事,讲的是她父亲小时候用弹弓打这些鸟是多么厉害。我们婚后的第二年,安东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不知怎的,我们决定尝尝安东小时候常吃的一道菜,以此来纪念他,尽管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捕鸟,更不用说怎样去烹饪了。最后,我记得是出租车司机穆斯塔法毛遂自荐来帮我们解决了问题。鸟肉是在公用烤炉的铸铁锅里慢炖,然后作为一道黏稠的炖菜的一部分被吃掉了。这种鸟颜色很深,好似肝脏一样,更奇怪的是空心的骨头在我嘴里碎裂时的脆响。我现在才知道它们都是濒危的迁徙鸟,是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偷偷摸摸吃的盘中餐,但他肯定知道它们在法国是受保护的,知道它也是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这样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发起的运动所要保护的对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这种鸟,而且也没必要再尝试了,那次经历终生难忘。这种体验总是让我不由得心里暗暗哀悼。
1837年,一个名叫威廉•王尔德的爱尔兰医生访问了伯利恒,注意到主诞教堂下面的洞穴和伯利恒的公用烤炉极为相似。一段弧形楼梯通向教堂下的洞穴,楼梯的线条意味着洞穴一直是隐蔽的,你不走到底,便发现不了它。在地下室,你会发现在洞穴的侧面墙上凿出了一个低矮的小房间,里面镶着大理石,挂着一个金色的香炉。在角落里一个星形的银盘标示出马利亚生下基督的地方,而这个角落看起来确实像烤炉的口。或许这仅仅只是个巧合,一如鸭嘴兽的嘴像鸭子的嘴,但是王尔德把这种相似性看得很认真。他将这视为一个证据,证明这个洞穴不可能是伯利恒原始商队旅店的所在地,但反驳这一观点也同样容易,旅行者必须吃饭,旅馆便提供食物。
挂在铁链上的油灯照亮了洞穴,油灯的烟熏黑了藏在原始石墙上的挂毯和画。墙面也是黑色的,因为1869年在洞穴里发生过一场火灾,毁掉了王尔德曾看过和描述过的那些赏心悦目的画作。(圣方济各会的网站称,洞穴的墙面上覆有石棉,是法国送的礼物,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觉得石棉早就被移走了。)这个洞穴实际上有两个楼梯,角落的两边各有一个,它们的弧形弯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以至于楼梯互为镜像。在最繁忙的日子里,当朝圣者排成长队时,一个会作为洞穴的入口,另一个则是出口。洞穴呈菱形,在图表上看有如子宫,而两侧的楼梯则如同输卵管。我敢肯定这种相似纯属巧合,但是这种联想曾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那是在潜意识中提醒人们,伯利恒是由女性建造的。
威廉•王尔德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当年他造访伯利恒时,是作为一名拥有私人游艇的老年病人的私人医生随行的。他对此行的描述,记录在《航行漫记》(Narrative of a Voyage)里,首次出版是在1840年,后来在1844年英国人帮助奥斯曼人从埃及人手中夺回这个国家之后,又进行了修订。此书第二版的副标题是“对埃及和巴勒斯坦现状及其前景的观察”,这表明中东问题已经开始冲击英国民众的良知。圣地一直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就在10年前,任何没有携带奥斯曼帝国文件访问伯利恒的人都只能伪装后偷渡边境,就像1920年代另一位爱尔兰医生理查德•罗伯特•马登所做的那样。
王尔德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及其前景的观察是很随意的。他提到,不久前穆斯林的法瓦格拉赫家族被驱逐出了伯利恒,但当他从埃及当局那儿得知,这是因为他们与基督徒长期不合时,他就信以为真了,完全不知道最近在拜特贾拉和希伯伦发生了叛乱和大屠杀。王尔德当时才20多岁,他在书里对马里河谷街喷泉旁的年轻女性的描述,远远多过对宗教或政治的描述。王尔德被这些女性的美貌所吸引,不一会儿就开始跑偏,长篇大论地建议所有妇女都头顶水罐,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好的姿态、体力和优雅。这些关注点是如此露骨,以至于人们好奇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和奥斯卡•王尔德的母亲结婚时,他已经与两个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似乎是他的家人打发他去了地中海,这样他就不会跟人生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让奥斯卡有个非婚生的兄长。
午餐往往是炸豆丸子;我最爱的便是位于马槽广场的那家名叫埃夫泰姆的店。如果你认为像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这样的国际政治家可以算得上是名人的话,那么这家店的墙上可谓挂满了到此一游的名人的照片。我也很喜欢藏在拜特贾拉露天市场后面的一家普通小店。多年来,这家小店的墙上仅有一张亚西尔•阿拉法特与萨达姆•侯赛因握手的褪了色的照片,还有一个印有东正教圣徒的日历。我不知道店主的这种没有章法的混搭是希望吸引什么样的人,尽管他家的三明治很好吃,而他本可以在墙上挂一张以色列政治家的照片,这样人们还是会停下来在此吃顿午餐。当他打开皮塔饼的袋子时,一只手在沙拉上方比划着问道:“你想要什么,都要吗?”我总是都想来点——沙拉、辣酱、芝麻酱、泡菜。食品历史学家似乎都觉得豆类植物和鹰嘴豆搭配的菜肴,就像杂拌豆与炸豆丸子放一起一样,可能源于很久以前的埃及。
奥斯曼帝国对伯利恒的影响一直存在于游牧骑兵的烤架上。阿拉伯语中的沙威玛(Shawarma)指的是“烤肉串”(doner kebab),这就像希腊语中的gyros(陀螺)是指旋转式烤肉一样。当我不想吃炸豆丸子的时候,可能就会去新路上那家名为“沙威玛之王”的店里,或者去拜特贾拉小山的半山腰卖鱼的店旁边的那家。我可以选鸡肉或肉,也就是羊羔肉,不过现在羊羔肉常常被牛肉取代。牛肉是在附近的米格达尔奥兹定居点的大棚里工业化养殖的,而羊羔肉贵得让人望而却步,这是由于为了建定居点,牧羊人都被赶出了牧场。伯利恒的屠夫只经营一种肉,所以在拜特贾拉的小露天市场,卖鸡肉的、卖牛肉的、卖羊羔肉的和卖猪肉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小镇)屠夫就这么面对面地坐在十字路口的四个点上。
1841年,奥斯曼人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下,从埃及人手中夺回了巴勒斯坦,英国人的动机引人怀疑。11月3日,英国炮舰轰炸了阿卡,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一个弹药库,火光冲天,轰掉了半个城市。英国人采取行动,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奥斯曼帝国,能够在阿富汗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次干预事与愿违,由于伯利恒发生的一起事件,战争终究还是爆发了,因为法国和俄罗斯都争当主诞教堂的监护人。法国人与伯利恒的方济各会修士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俄罗斯人则试图宣称对洞窟上方的东正教礼拜堂有所有权。总之,没有一种解决之道能让双方都满意。
1847年,标志着基督诞生地的那颗原始的星星被人从地面上被撬走,不翼而飞。银盘上的拉丁文被天主教徒视为领土标志。没人怀疑东正教僧侣就是小偷。为了加紧争夺对洞窟的所有权,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这一次双方都亮出了各自的炮舰。法国人派出一支海军部队前往君士坦丁堡南部的达达尼尔群岛,俄罗斯人则从北部的黑海威胁这座城市。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法国和英国日益相信俄罗斯人会入侵君士坦丁堡并推翻苏丹。1854年2月,向俄罗斯发出的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回音。次月,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就因为伯利恒的一颗银星,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奥斯曼帝国被定性为“欧洲病夫”,是英国向俄罗斯宣战的原因之一。标签就这么粘牢了,但压根就不准确。奥斯曼帝国本质上并非弱者,也不比西方国家更不道德或更颓废。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它就处于不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始于1839年的坦志麦特改革废除了包税制。政府还保障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比英国对其帝国的非英国臣民的态度,或者美国对非洲人的工业奴隶制度的依赖,这是一个积极的启发。到了1908年,奥斯曼人认识到了代议制政府的必要性,这让巴勒斯坦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议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奥斯曼人拥护自由贸易,这对伯利恒的圣像及纪念品生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类生意主要是由达布多布家族、贾克梅第家族、杰西尔家族、哈兹伯恩家族、汉达尔家族、米克尔家族、佐格比家族、卡坦家族,甚至还有穆斯林的肖克家族经营。(在埃及人被打败后,肖克家族在伯利恒重建了他们的社区。叛军领袖哈利勒•肖克的玄孙是伯利恒大学的教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些家族建起了一个个贸易王国,其范围从菲律宾、澳大利亚延伸到乌克兰、俄国,从法国延伸到美国、拉丁美洲,并与这些家族一起在国际贸易展上展出了它们的商品。伯利恒人被列为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1903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的参展商。伯利恒的这些家族跟随朝圣者返回家园;比如卡坦人,在基辅建立了前哨。他们为寻找原材料走遍了全世界,在菲律宾发现了一种外壳较厚的新品种牡蛎,这种壳上可以雕刻出更多的细节,随后他们在菲律宾开设了办事处。
随着这些家族向海外办事处派出使者,这种在全球建立起的网络导致伯利恒人流散海外。19世纪末,奥斯曼人开始征召巴勒斯坦人来帮忙镇压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叛乱。伯利恒的家族采取的对策是将他们的儿子送出国以躲避征兵。即便如此,迁往他地的移民还是会经常回去,伯利恒人习惯了来回走动。
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因为军事占领限制了工作机会,也让人失去了行动自由和婚姻自由:如果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与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就会丧失在以色列的居住权。
伯利恒犹太人的大流散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拉丁美洲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1920年代,伯利恒人和拜特贾拉人成立了智利超级联盟的一支伟大球队:帕勒斯蒂诺足球俱乐部队(Palestino)。2004年,萨尔瓦多举行总统大选时,就有来自纳贾吉拉赫家族的反对派候选人参与角逐,分别是左翼人士沙菲克•汉达尔和获胜者安东尼奥•萨卡,后者是一位奉行保守派政纲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塔拉杰梅家族中有一家姓科曼达里的,踏足了拉丁美洲生活较为阴暗的一面:这家的一个分支在1980年代出了多位贩卖可卡因的大毒枭。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巴勒斯坦人打开了世界的大门,那么它也向世界开放了巴勒斯坦。即使在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那场争端仍在继续。英国的影响力最初仅限于个人和慈善机构。早在1841年,英国慈善家蒙特摩西•蒙蒂菲奥里就获得了伯利恒拉结墓的租赁权。
至少从公元4世纪开始,圣祠就一直是基督徒朝圣的一个目的地,这一点圣杰罗姆在给罗马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在蒙蒂菲奥里的时代,圣祠是穆斯林墓地的一部分,就在希伯伦路的一个路段,那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纪念品商店和餐馆的所在地。圣祠是一个带圆顶的侧面开放式亭子,有些年久失修。蒙蒂菲奥里在两侧做了填充,使得其构造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坟墓。(当蒙蒂菲奥里100岁去世时,被安葬在他英国家中的一个照此仿建的坟墓中。)我在1994年第一次访问伯利恒时,圣祠依然是座很吸引人的带有两个房间的平房,被树荫遮蔽着,对面有一排餐厅。坟墓就立在两边绿树成行的墓园里,外面是阿伊达难民营。如今,墓地被一堵高高的混凝土墙包围,只能从附近一些酒店(包括英国艺术家班克斯在2017年年初开的那家)的顶层去看,即使这样,也只能窥见其圆顶的轮廓。以色列人修建混凝土墙是为将墓地与伯利恒切割开来。墙沿着希伯伦路延伸,像一条阿米巴虫盘在建筑周围,还伸展着卷须吸附外来生物。20年前,我第一次参观拉结墓,当时这个地方不仅吸引了以色列游客和外国游客前来参观,还有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她们祈求拉结调解她们的家庭纠纷。自从拉结墓被盗后,我只去过一次,发现那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乌泱泱的讲意第绪语的哈西迪教派的人,他们乘长途车来到这里,将圣祠划分为男性参观区和女性参观区。
英国对于干涉巴勒斯坦这件事不仅坚定而且劲头十足,也许这就是他们最终对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原因。那时即将上任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紧随埃及人之后访问了巴勒斯坦。随着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全民痴迷的对象,迪斯雷利效仿王尔德,在其小说《坦克雷德》(1847)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迪斯雷利是一名西班牙裔犹太人,他的父亲与当地的犹太教堂闹翻了,全家人受他父亲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迪斯雷利的小说以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和解为主题——“我将我的灵魂托付给耶稣基督,以及西奈的神,我将为神湮灭。”这是小说中的人物、维多利亚时代的坦克雷德的话,说完他向一个充满敌意的贝都因人的两眼之间射出了子弹。
迪斯雷利的小说中加入了数量惊人的杂志文章、平版印刷画、照片,并提到了一些关于巴勒斯坦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充斥着英国和美国。即使伯利恒成为焦点,人们最感兴趣的也莫过于圣诞节。英国的炮舰帮助巴勒斯坦获得解放的那个月,身材娇小的21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那年圣诞节,她和阿尔伯特亲王以小家庭——三口之家——的形式予以庆祝,就像最初神圣家族那样。1848年,《伦敦新闻画报》在一幅平版印刷画中描画了这一皇室家庭与他们的三个孩子聚集在一棵树旁的样子。这对皇室夫妇重塑了英格兰的形象,圣诞节从此成为英国的一个重大节日,有我们如今所知的所有过节元素:布丁、阿尔伯特亲王从他的祖国德国引进的圣诞树,以及多半在伯利恒制作的反映耶稣诞生场景的木雕等。圣诞节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庆祝活动,甚至还有了这个节日专属的桂冠诗人查尔斯•狄更斯,自1843年起,每一年狄更斯都要写一个圣诞故事,作为献给自己祖国的礼物。狄更斯使得圣诞节成了当时的道德试金石:知道如何过圣诞节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英德联姻促使英国圣公会与德国路德教会设立了一项联合项目,即在耶路撒冷设一位新主教。这一想法还远未得到大众的支持,甚至需要议会通过法案来确定。约翰•亨利•纽曼因此皈依了天主教,以示抗议。然而,在1842年1月,第一位英德主教抵达了耶路撒冷,他就是迈克尔•亚历山大•沃尔夫,一个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而且当过拉比,26岁时他在都柏林皈依了英国国教。众所周知,主教迈克尔•亚历山大与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简称犹太人协会)合作密切。1836年,该协会在埃及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开办了一个医务室,最终扩建为拥有24张病床的一家医院。然而,该协会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由年轻的夫妇约翰•梅苏勒姆和玛丽•梅苏勒姆赞助的,他们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梅苏勒姆家希望在伯利恒开一个农场,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定居者。
梅苏勒姆一家是通过一位名叫塞缪尔•戈巴特的瑞士神职人员皈依基督教的,戈巴特于1846年接替迈克尔•亚历山大成为耶路撒冷的第二任主教。梅苏勒姆一家在耶路撒冷经营着一家小旅馆,那是该城第一家欧洲人开的旅馆。
一天,约翰•梅苏勒姆骑马经过伯利恒,误打误撞来到了阿塔斯。这个村庄一片荒芜,而梅苏勒姆迷惑不解的是,竟然有人会遗弃这么美丽的地方。让他更加困惑的是,他发现整个村庄的人都流离失所,住在所罗门水池上方一个狭小的穆拉德要塞。阿塔斯村民在要塞里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了4年,他们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梅苏勒姆这才知道,他们与塔马利赫贝都因人有着血海深仇,贝都因人向他们索要一大笔钱才肯善罢甘休。双方争端的根源在于十年前与埃及之间的战争。埃及人把塔马利赫人和法瓦格拉赫人赶出伯利恒之后,阿塔斯的村民被雇来代替法瓦格拉赫人保护耶路撒冷的渡槽。随着埃及人的战败,村民们发现自己被打上了叛徒的烙印,就这样陷入了绝境。
梅苏勒姆决定筹款付钱给塔马利赫人,并自己租下了农田。他与犹太人协会的另外两个成员合作,共同制订了一项计划。这两名成员分别是自1846年以来担任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的詹姆斯•芬恩,以及詹姆斯的妻子伊丽莎白,她负责为项目筹集资金。塔马利赫人被钱说服了,阿塔斯的土地被租给了一个新的农业定居点,阿塔斯的村民再次受雇为农场工人。犹太人协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约翰•斯坦贝克的祖父和一个姓巴登斯伯格的德国家庭也加入了梅苏勒姆家的定居点,一直在阿塔斯村住到20世纪。
在约翰•梅苏勒姆的儿子彼得受芬恩雇佣到英国领事馆工作后,约翰•梅苏勒姆的生活从此变得糟糕起来。彼得是个愤青,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他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发生了冲突。一天晚上,他在去伯利恒的路上遭到伏击被杀害。约翰•梅苏勒姆为此指责詹姆斯•芬恩,说是对方将他的儿子置于危险的境地。
双方的争执升级,焦点开始转移到阿塔斯的所有权问题上。阿塔斯到底是属于建立农场的梅苏勒姆?还是属于不断在通过自己的慈善工作为定居点提供资金的伊丽莎白•芬恩?其中一名主要的捐资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小儿子亚瑟王子。1863年,梅苏勒姆对伊丽莎白提起民事诉讼,当该案在领事法庭审理时,芬恩做出了有利于他妻子伊丽莎白的裁决。英国外交部推翻了这一带有偏袒的决定,与此同时,芬恩被予以解职。这对夫妇搬到了伦敦的布鲁克格林,穷困潦倒的芬恩后来在此去世,伊丽莎白成立了“贫困绅士援助协会”。
在新路的起点、马槽广场的入口处,有一家新开的意大利冰激凌店。该店归方济各修会所有,并有一个独特的吸引力,那就是教皇方济各的专车就停在露台上,任何人都可以上去试坐,亲身感受一下。我坐在教皇座驾的人造革座位上,吃着我会在午后吃的冰激凌蛋卷,看着游客们拖着沉重的步伐从我面前走过,向山上的教堂走去。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坐长途车来到这儿的。20年前,这些长途车会停在马槽广场,但如今被引导到新路上的一个多层停车场。这样做是觉得如果游客不得不多走几步的话,他们就会欣赏到更多的小镇风光。游客们在耀眼的阳光下眯着眼睛,汗流浃背,在以色列导游的指点下排着队,听着有关小镇旅行安全的听来吓人的警告。
教堂是主要的一站,游客们最多在此停留一个小时,然后是参观拜特萨霍和两个对立的教堂——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堂——中的一个。从伯利恒到拜特萨霍这一路,意味着把游客们从该地区的最高点带到了最低点,这无意中也揭示了伯利恒小镇的极不寻常之处。这是小镇生活最不理想的地方:没有天然水源,却又坐落在山顶之上。
在更广阔的伯利恒地区,最古老的建筑群总是能在半山腰的阴凉处而不是在正午顶着烈日的山顶找到。干河谷底部的冲积土被翻过,种上了卷心菜和莴苣等市场作物,就像在阿塔斯和夫钦河谷一样。朝南山坡日照充足的地方有葡萄园,一如在吉洛定居点下面的克雷米桑山谷中现在废弃的梯田。小山的上坡布满了果园和橄榄园。伯利恒在山顶上的位置表明它应是一个军事观察点,而不是一个村庄。它是个驻军点,与它所指挥的山谷的农业耕作生活相去甚远。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游客来到伯利恒,在山顶上的一些地点进行了某种宗教崇拜仪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院长亚瑟•斯坦利
在1852年至1853年的圣诞节期间朝圣时,已经是一位作家和名人了。他把这段旅程写了下来,以《西奈与巴勒斯坦》(1856)之名出版,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斯坦利希望借此拂去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尘埃,打消带误导的观点,从而给《圣经》研究带来新的严谨。与杰罗姆一样,斯坦利想“回到《希伯来书》”,但不是通过文本,而是通过游览宗教圣典中所描述的土地。斯坦利想从《圣经》中族长的视角来看待巴勒斯坦。为此,他爬上了每一座可以攀登的山,去饱览大好风景。
斯坦利想象着自己所站的是摩亚人被打败的地方,是约书亚过约旦河的地方,是摩西坐着看风景“从基列全地看向但城,还有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和玛拿西全地,看朱迪亚全地,并从那里极目远眺地中海、南方、有‘棕榈树之城’称号的杰利科的平原山谷,直到避难所(Zoar)”。每一幅景象似乎都证实了《圣经》的真实性,如果他再仔细看一会儿的话,也许会的。这些爬山探险,借用德里达的话说,是“在真理面前兜圈子”。斯坦利以自己是一个进步的维多利亚人而自豪,认为自己是一个讲科学的人。然而,他的方法是对科学方法的一种模仿。他来到巴勒斯坦,相信自己会找出《圣经》的真实所在,每次奋力爬上一座小山,他都会让眼前的风景既符合《圣经》的文本,又符合自己已有的信仰。尽管斯坦利自己先入为主,他倒严厉抨击起了老探险家。他特别批评了相互对立的拉丁教会和东正教教会的传统,认为对立这个错,根源在于圣海伦娜。斯坦利嘲笑海伦娜发现了一个洞窟,就以为这个地方涵盖了基督生活从天使报喜到牧羊人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哺育幼婴到逃亡埃及。他写道:“当巴勒斯坦的宗教落入欧洲人手中的那一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变成了一种洞窟宗教。”即使是被谋杀的无辜者,也有洞窟在主诞教堂的地下。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看到一堆骷髅和骨头真是令人心惊胆寒。当这种寒意散去,眼睛回过神来,你会意识到这些人类遗骸太大了,所以不可能是婴儿的;这些实际上是伯利恒一个古老墓地里未分类的尸骨。
序 圣诞布丁001
第一章 游牧部落与恋人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第二章 气味、香料及化学品
——铁器时代
第三章 伯利恒与基督
——古典时代
第四章 海伦娜教堂
——基督教罗马时期
第五章 皇帝的新教堂
——拜占庭
第六章 商人到十字军
——从伊斯兰的征服到十字军的城
第七章 马穆鲁克与奥斯曼
——从13世纪至19世纪
第八章 英国人
——维多利亚时代至二战时期
第九章 约旦
——1948—1967
第十章 以色列
——从1967年到奥斯陆事件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
——奥斯陆之后
第十二章 定居者的未来
第十三章 伯利恒之未来
附录 定居点名录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