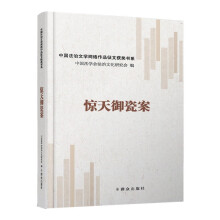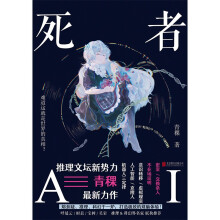第一章 学术思想渊源、流变与转向
自20世纪初,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实践中,徐中舒直接继承晚清桐城学派“博求慎取”“穷原竟委”的学术风尚与“唯是之求”的治学原则,以及王国维、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与科学的治学门径,并自觉借鉴傅斯年、李济、陈寅恪等学者的新汉学理论与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建立起圆融通博而又富于鲜明个性特征的学术思想。晚清桐城学派的学术风尚与治学原则和王国维、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与科学的治学门径分别构成徐中舒学术思想的两个重要源头。相对于以上的两个重要源头,傅斯年、李济、陈寅恪的新汉学理论与方法,则是徐中舒学术思想的重要支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徐中舒先生通过参加政治学习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以及长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自觉完成了从近代新史学向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转向,并直接影响到其学术思想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徐中舒由此前重史料、考据转向以史料、理论并重;由重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兼顾;进一步重视民族史研究,继续完善并积极实践将文献记载、田野考古资料相结合,再参以民族学材料进行互证的古史多重证法等。
徐中舒(1898—1991年)先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徐中舒在先秦史、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明清史、巴蜀文化与西南地方史等多个学科领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并由此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代宗师的崇高地位。然迄今为止,对徐中舒学术思想及徐中舒史学的研究,学术界尚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和重视,已有的研究从总体上看缺乏一定的深度和系统性,诸多相关专题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徐中舒学术思想渊源及流变为徐中舒学术思想和徐中舒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科学领会与准确把握徐中舒学术思想渊源及流变,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第一节 晚清桐城学派“博求慎取”“穷原竟委”的学术风尚与“唯是之求”的治学原则——徐中舒学术思想渊源之一
徐中舒于1898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市),1914年2月考入安庆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1月毕业。徐氏出生和早年读书的安庆,历史悠久,文风昌盛,人才荟萃。清代以来,崛起于此,以文统源远流长、文论博大精深、著述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的桐城古文派,作为清代文坛上*大的散文流派,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徐氏回忆说:“清朝光绪年间,桐城古文学派的文章经曾国藩的提倡而风行全国,作为桐城派故乡的安徽,影响更是深刻。”j迄徐氏入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前夕的清末民初,桐城古文派已进入末流期,其学术风尚也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而呈现出颇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事实上,此种变化可以上溯至嘉庆年间。方东树所著《汉学商兑》,批判清代汉学之失,极力为宋学辩护,“但其总的立意却在于为宋儒辩护的同时,主张汉宋兼采”。方氏之后,“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迄咸、同年间,湘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则逐步建立起调和汉宋、兼收并蓄的学术思想。李鸿章曾充分肯定曾氏“兼综汉宋”“持论*为平允”的治学风尚: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为平允。
无独有偶,钱穆亦对曾氏“平正通达,宽宏博实”的学术取向作出如是评价:
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龂龂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
之后,曾国藩的“平正通达,宽宏博实”学术思想为被学术界称为晚清桐城学派*后一位宗师的吴汝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吴汝纶传》说:
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原而竟其委。
吴氏指出,汉学、宋学,各有缺陷:
窃谓古经简奥,一由故训难通,一由文章难解,马郑诸儒,通训诂不通文章,故往往迂僻可笑;若后之文士,不通训诂,则又望文生训,有似韩子所讥“郢书燕说”者,较是二者,其失维钧 唐宋文人,于六经能抉摘隐奥矣,其所短则古训失也。朱子于理学家独为知文,其说得失参半,又其文事未深,故古人微妙深远之文,多以后世文字释之,往往不惬人意。
与以往清儒治学风尚迥然有别,吴氏指出:“义理、文章、训诂,虽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则为极至之诣。”基于此,吴氏对清代学者鄙弃宋学、袒护汉学、偏执一端的学术风尚提出批判:
我朝儒者鄙弃其说,一以汉人为归,可谓宏伟矣,唯意见用事,于汉则委曲弥缝,于宋则吹毛求疵,又其甚者,据贾、马、许、郑而上讥迁《史》 不能观其会通,而斤斤于汉儒之家法。
吴氏将“博求慎取”“穷原竟委”的学术思想与“唯是之求”的治学原则贯穿于其宏富的学术论著中。吴氏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尚书故》一书,“用近世汉学家体制,考求训诂,一以《史记》为主,《史记》所无,则郢书燕说,不肯蹈袭段孙一言半义”;《易说》“则用宋元人说经体,亦以训诂文字为主,其私立异说尤多,盖自汉至今,无所不采,而亦无所不扫”。在以上学术思想与治学原则的主导下,吴氏探索出了一条研治经学的新思路、新途径。
吴氏关于“博求慎取”的学术思想在其学术研究中,还体现在其对于新知、真知的孜孜追求方面。如吴氏根据当时的天文学新知,对《丰卦》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虞翻注“日蔽云中称‘蔀’”提出批判:“但云去地至近,日去地至远,‘日在云下’,乃昔人天算之疏,无是事也。”又如《尚书 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吴氏论及:“以岁、月、日、星,况上下之相应,非谓君行如此则天应如彼也。自大、小夏侯等推《五行传》,刘向、歆父子傅以行事,而《洪范》一篇,遂为灾异荒怪之嚆矢,班氏取以入史,此其失也。后儒集录伏生《大传》以《洪范五行传》为伏生之作,此考之不审也。 伏生解五行,以为是为人用,不作为天行气之语,其不妄推灾异如《五行传》所言明矣。星之‘好风好雨’,中国经典旧说,今西域天文家不谓然也。”吴氏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在对儒家经典作出新的阐释的同时,也给经学研究带来了一些崭新的气象。
徐氏在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学习三年,师从晚清桐城学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胡氏直接继承吴汝纶的学术思想与治学原则,其著述以哲学为主,“学问渊博,为世所宗,尤深于老庄之学”。胡氏“除精研哲学外,于其他学科,未尝不津津探讨,以求与哲学中诸问题互参解答也”。徐氏反复强调说,安庆初级师范学校三年所受的中等教育,是其“一生*重要的阶段”,“在这里我受桐城派的影响很深”:
一九一七年我在初级师范毕业,这时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重要的阶段。我在这里啃了些中国旧书,在这里我受桐城派的影响很深。学校里学古文只是练习写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启示,就不能以此为满足。桐城派要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我就要求从这三方面充实我自己。
此后,师从徐中舒先生四十余年的唐嘉弘先生,谈到徐氏的治学方法和学风:
徐老一贯事必求根,言必求据,穷源究委,上下求索;常将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诸学科的材料、观点与方法,紧密结合,融会贯通,综合分析,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惟陈言之务去”,能成一家之言,创见甚多,新颖笃实。
唐氏以上所论,是颇为切合实际的,唐氏将徐氏的治学方法和学风视为“史语所的学风及治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但追根求源,则不难看出,徐氏日后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优良学风和建立的科学治学方法,则清晰地打着晚清桐城学派“博求慎取”“穷原竟委”的学术思想与“唯是之求”的治学原则的深深印记。
徐氏受桐城学派的另一重要影响,是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和理论:
我因为学桐城派古文,就读了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译》《群学肄言》这一类的书。因为严复是吴汝纶的弟子,他是用桐城家法来翻译文章的,因此,我就开始接受了些资产阶级的教育,社会进化论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理论,从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动摇了。
现代西方思想和理论对于日后徐氏走上新史学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彻底改革旧中国的思想弥漫全国 那时整理国故的呼声很高,古史的讨论很热烈,这都很合我的脾胃。我的思想也由主观的尊崇国学转变为客观的整理国故派了。我一方面接受新理论,把学以致用分裂开来。 一方面我开始研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我开始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传统的尊经观点,我是没有了。 到一九二五年我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告一段落,我把以前所受的封建教育与资产阶级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为新汉学奠立了基础。
综上可知,安庆初级师范学校的三年,在晚清桐城学派“博求慎取”“穷原竟委”的学术思想与“唯是之求”的治学原则的深刻影响下,徐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初步培育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建立博涉基础、综贯会通、穷原竟委、言必有据、独辟蹊径、务求创新的学术思想。与此同时,在现代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下,徐氏自觉走上与传统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