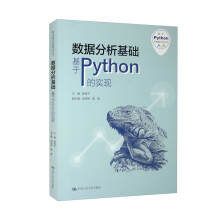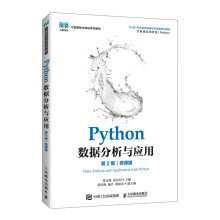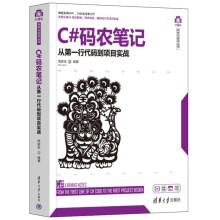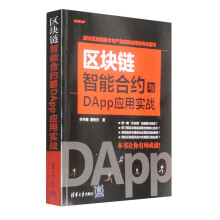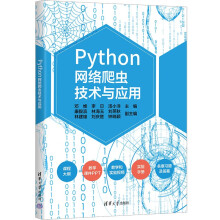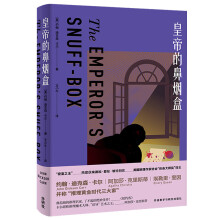过了五十岁之后,常常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白天想到这些人和事,晚上就会梦见他们。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最近一入睡就会做梦,梦见我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不同时期的同学和朋友。而我的博士导师侯维瑞教授则几乎天天都会梦到,每次梦醒之后,总会感到惊奇: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侯先生的音容笑貌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先生不时入梦来,莫非跟我近来一直在阅读先生著译的书籍有关?还是在提醒我疫情期间禁足在家须不忘多读书勤写作?
侯先生招过的博士生数量不多,加在一起不过十来人。我能忝列先生门墙,与有荣焉。而我可以说是先生所招学生中唯一从入学到毕业全程跟随他的学生,按古人说法,整整三年得以从先生游。在我之前和之后入学的同门正好碰上侯先生不在国内,我同一届的何伟文师姐(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就读期间怀孕生子离开过一段时间。不过,我虽是侯先生全程参与培养的学生,却也是他所有弟子中最没有出息的,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惭愧不已。
侯先生是教育部批准的博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据先生生前告知,他招收的第一个博士是原杭州大学的教师潘大安教授(现供职于美国一所大学,大概也到了退休年龄了。)我是1995年开始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的,当时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不久,我还不认识先生,只读过他撰写的两部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我国著名的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佐良先生生前对侯先生这部著作十分欣赏,曾在多个不同场合跟多人提及,说此书对读者了解现代英国小说助益良多)、《英语语体》和一部译著《华盛顿广场》,还有发表在各大学术刊物上、用英语撰写的文章,但对他精深的学问却是心仪已久了。我之决定报考博士,是在我的硕士导师、英美戏剧研究专家汪义群教授的鼓励下才下定决心的。我硕士毕业留校,与汪义群教授成了上外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与侯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还是汪老师亲自带我去的,也是汪老师替我介绍情况、说明我继续深造的理由等,也许是汪老师说了我许多好话,他的溢美之词给侯先生留下了初步的印象,侯先生竞一口答应,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
报名时要提交硕士论文和已发表的科研成果,侯先生仔细阅读了我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后来退还本人,我看到页边空白处有大量的评论和批注,均出自先生手笔)《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意识》,以及我1994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上的两篇论文,还有发表在《外国文艺》上的译作。读后先生约我见了一面,先是讲了一番鼓励的话,随后话锋一转提醒我说:做学问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做到心无旁骛。他让我回去好好准备,多练习英文写作。我这时大胆地向先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怕二外考试通不过。他便问我二外学的是什么,我回答说大学期间学过两年的日语,研究生期间学过一年法语,但两门外语都只是懂点皮毛,经不起考试。先生略为沉吟了一下,说道:你先好好准备,到时再看情况吧。这个情况就是我二外差了几分没有及格,侯先生得知后专门去研究生部说明原因,最终让我顺利地获得入学资格。行文至此,请允许我旁逸斜出一下。我担心二外考试通不过也跟汪义群老师提起过。汪老师二话不说,带着我去拜访了当时担任西方语学院院长后来又担任上外校长的曹德明教授,曹校长具体给了我什么建议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了一句:二外法语不是我命题的,即使是我命题也不能告诉你什么,回去好好准备吧。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不敢忘却这两位老师的提携之恩,他们是我为人为师的榜样,永远值得铭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