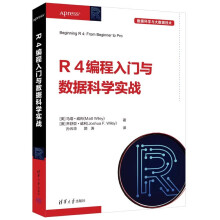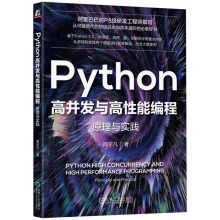创意写作始于对语文学的反抗,又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卷土重来,致力于修辞学的文学价值、教育价值的重建。其贡献是最终形成了现代英语领域。传统学术观点并不承认文学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现代英语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可能。随着现代英语研究的开展,反对的矛头由语文学转向了修辞学。在发现旧的学科漏洞百出后,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重建,并将其命名为“文学写作”。
在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写作被认为是一个混杂无序的领域,但它接下来的任务并不是使原初目的含混不清。文学写作给了创作教学第一次全面成功的机会,它不是将写作局限为高校课程中不起眼的一部分,而是(用学科奠基者的话说)“不可或缺的部分”。19世纪最后25年,在摒弃了结构主义理想之后,哈佛大学明确表示:文学研究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文学创作的开始。正是如此,几年后有评论者指出:“流畅性排在一长串文学要求的最前面。”实际上,此后创作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因文学性过强而遭到批评的结果——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不那么杰出的人才。与此同时,对文学流畅性的要求已经在创意写作中得到落实。文学写作确立了高校写作的自主性,并从文学性和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写作课程提出要求;这也是创意写作成为正式研究课题的先决条件。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高校对创意写作本身的需求并不大,因为文学写作与创意写作在当时是一回事。创意写作的真正兴起,是在文学写作转入非文学状态之后。前者甚至被视作后者的再现,区别在于前者高举着一个更加与众不同的文学旗号,且指向着写作的最初目标(但这一目标已经被逐渐抛弃)。
“文学写作”的名称,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也曾偶尔使用,但此前美国高校所教的写作,与这个名称完全不相称。半个多世纪里,“写作”被公认为拉丁文写作,同时也是拉丁文学研究的内容。学生写文章时运用语法规则——或者说,从古典文学中获取风格和种类,有时候甚至用英文写作,而其目的与用拉丁文写作无异。写作的动力,在于表现对语言的掌握水平。这种写作从属于语法练习、拼写训练和修辞规则识记。即使在写作作为课程核心的情况下,也着重培养学生在论述过程中的简洁度、敏感度、精确度、正确性及完整性。不鼓励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想象,而是极尽所能地避免出现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有评论者表示:“写作变成了语言研究的基础……”
新的文学写作作为修辞学研究的发展,只延续了其结构体系,进入了修辞学为美国高校写作教学而开辟的领域。换句话说,新写作与传统修辞学相去甚远,它不涉及转喻、论点、言语的社会背景、对实践结果的追求或者对作品、种类、风格、记忆、演讲的传统细化标准。事实上,文学写作可以称为“写作教学的结构主义化”(前提是这一说法能被人接受),以拒绝作为19世纪美国高校修辞学附庸的传统课堂教学。首先,它不主张学生使用英语语法手册,从而淡化语言准确性训练;其次,又不注重口头表达,因而淡化对交际能力的培养。文学写作并非对原有的高校修辞学进行发展和更新,而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文学写作是对修辞学的文学化改革。在《十九世纪修辞学(北美篇)》(Nineteenth-Century Rhetoric in North America)一书中,南·约翰逊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大部分修辞学理论的基础都是“习得批判性眼光,就等于获得了更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更高的领悟天分”的“纯文学设想”。约翰逊还说,这种纯文学设想引发了“全面的修辞学定义”,使修辞学由论辩、演讲艺术扩散到更具文学性的话语之中。更准确地说: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纯粹的修辞研究(或是我所说的“结构主义”)是以文学写作的名义确立的;认为开设该课程的直接动因是写作而不是演讲,根本目的是表达而非准确度——这种观点同样是“纯文学的”。
因此,新写作的转向包括两方面重要的制度改革:第一,学生的学科论文不再指定主题;第二,不在课堂上高声朗读。在原有体系中,学生需要组织思想,回答诸如“灵魂的永恒性是否可证”或“灵魂是否一直思考”之类的问题;而在新体系中,只规定了类型或手法,主题则交由学生自己处理。从传统修辞学的观点来看,“创作”并不能通过新写作课程习得,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品位与天分,要遵从浪漫主义的创造天赋论。准确性与指定的主题也由此不再重要,受到鼓励的是原始工作。由于新写作不需要朗读,原有的记忆、演讲方面的修辞学问题也就消失了。写作取代演讲而成为授课的主要形式。
演讲指导与新写作兴起于同一时期,起初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堪萨斯大学和密苏里大学是无学分课程,到9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为常规课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提出的,在语文学的压力下,话语艺术分成了两部分。早期的演讲教学的支持者,在所难免地因文学性话语篡夺了自己的地位而对其持有某种敌意。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