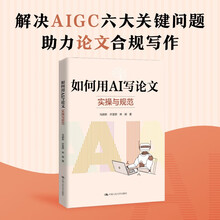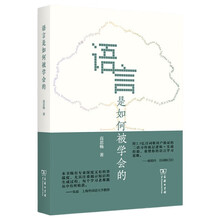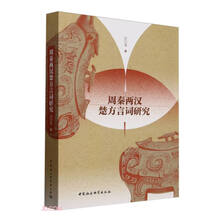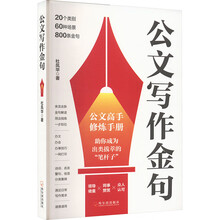第1章 基于翻译本质的理论翻译学构建
1.1 引言
1972年,霍姆斯(James Hol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确立了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将其定义为经验科学,所拟学科框架与研究范围具有里程碑意义。霍姆斯之后,Toury(1995)、Pym(1998)、刘宓庆(1999)、Munday(2001/2008/2012/2016)、William和Chesterman(2002)、谭载喜(2005)、曹明伦(2007)、Doorslaer(2009)等多名中外学者都曾通过重建学科框架,厘定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尝试引领翻译学良性发展。依据学科学,拟定学科框架是促进学科良性发展的手段之一,但从元学科层面进行科学哲学反思或更具有实际效果和理论意义。进而言之,如果翻译学隶属经验科学,那么,学科发展需首先重返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基于翻译本质进行学科的元反思。是则,本章以构建具有元学科意义的理论翻译学为目标,尝试回答为何要建构理论翻译学、理论翻译学构建为何要基于翻译本质、如何构建理论翻译学三个问题,通过重审翻译学经验科学本质,反思翻译理论的普遍解释效力,探讨翻译学的内部结构与关系,借以明晰理论翻译学的内涵外延及构建方法。
1.2 为何要建构理论翻译学
1.2.1 翻译学学科产生、历史与现状反思
如果“经验科学以描述经验世界的特殊现象以及建立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普遍法则为其主要目标”(Hempel,1952:1),作为经验科学的翻译学是从经验世界的翻译问题出发,基于翻译思想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翻译理论,并*终形成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明确的研究问题、科学的研究方法、普适性理论构建以及享有一系列同一价值观的科学共同体都应是构建和促进翻译学必不可少的因素。回顾翻译学的科学发展史,学界似乎更注重对科学方法的追求,轻视了上述其他重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奈达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借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探索翻译的“科学性”,力图通过细致的语言对比,证实翻译中存在的某种“对等性”,以此证明翻译的普遍性。虽然持续发展的翻译研究否定了“对等”的存在,但奈达等人所采用的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方式极大地推进了翻译学的学科创立,将翻译问题探索从经验主义的泥潭带出,为翻译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亟待解答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揭示了翻译与译语文化的种种联系。“转向”意味摆脱传统观念束缚,从已有观点出发,引入新的视角。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学派调整了研究起点,将翻译视作“译语文化的事实”(Toury,1995:29),明确指出科学研究范式是翻译学成为合法学科的基本条件。图里采用描述分析法,分析了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翻译家如何翻译本民族作家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尝试用综合法说明译者翻译策略和原作的选择是由本土既存规范决定的。描写学派对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同样可视作对翻译研究科学性的有益尝试,表明分析与综合这一辩证逻辑方法能描述关于特殊翻译现象的经验。受此影响,西方译界扩大了分析综合法的使用范围,引入了“后殖民转向”“社会学转向”等多重研究视角,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采用分析综合法得出的结论是否因此具有普适性?正如霍姆斯曾指出的:“有些看上去是普遍理论的理论,实际上只适用于西方文化区域。”(Holmes,1988:75)
威尔斯在反思翻译学的跨学科性时将翻译学比喻为“综合市场”,他认为当下翻译学充斥了无数价值观、标准和概念,关于翻译的讨论看似是永无休止的论争(Wilss,1999:132)。威尔斯的反思富有洞见,当下翻译学虽已显出一定的科学性,能用归纳、实验验证、观察、理论建构等多种科学方法分析和探讨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与问题,但经多次“转向”以及对其他学科方法大量复制借用后,翻译学自身的边界却开始变得模糊,暴露出碎片化、概念模糊、复制借用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的发展和扩张使得翻译这一原本清晰的学科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含混”(Brems et al.,2014:2)。这说明,上文所提及的明晰研究方法、研究问题、普适性的翻译理路和享有相同价值观和信念的科学共同体等问题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那么如何从当下的碎片化回归到常规科学的发展路径?对翻译研究开展元学科反思或是有效方法。
1.2.2 翻译学发展需要元反思
元学科反思首先是从反思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开始的。“元”(meta),有“本初”“开始”“基本”之意。将“元”的概念运用于学科的发展得益于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他于20世纪初提出了元数学概念,希望以整个数学研究为研究对象,超越数学研究的具体问题,元学科层面反思,是哲学层面的超越,是将整个学科作为研究对象,探明其预设问题,通过研究元科学概念和元科学问题,研究其中的认识论和逻辑问题,其根本目标是要推动学科的科学发展,消除学科内部的疑惑,促进正确知识的产生。
当下译学研究拓展的部分原因在于经验世界中的复杂翻译现象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一是包括语料库研究、本地化研究、职业化研究在内的新的研究领域不断产生,二是学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神经学、认知心理学等继续推进“翻译过程研究”“译者研究”等已有研究领域。但翻译学的科学发展还需要对经验进行分析、抽象和综合。单纯对现象的描述无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此同时,大量借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仅能说明翻译研究需要多重研究方法,还不足以将翻译学界定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因为跨学科的本质不在于借鉴和挪用,而在于对他学科知识的推进。因而,翻译学研究领域虽扩展,研究方法虽多元,其学科边界却越来越模糊。元学科概念的提出正是一种引导和规范,通过对翻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考证,重新确立翻译问题在翻译学内部的中心位置。
1.3 理论翻译学构建为何要基于翻译本质
在科学发展中,对知识和实在本质的反思是学科发展的终极问题,属形而上的思考,总由追问对象的本质而求得,需通过对学科内部的研究求得答案。
1.3.1 翻译本质是翻译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
从本体论层面看,翻译本质是开展形而上学思考、探求翻译有无普遍性这一哲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亦是其他一切翻译问题的起点。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提出“理念”或“型相”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到亚里士多德确立形而上学,再到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自己的哲学本体,本体已成为宇宙创生的动力因。“在已知的任何时期,科学在其前沿的运行总是遭遇到有关知识和实在本质的哲学议题,在具体科学中,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如何知晓它的问题会引发特殊的关注。”(郭贵春和殷杰,2016:1)哲学的根基是形而上学,本体反思是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要任务。理论翻译学的元学科反思以翻译本体论为基础。
本体有广狭二解。广义上,本体是一切实在的*终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获得。于翻译学而言,“翻译”本体探索是探讨翻译是否存在普遍性,是一切翻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翻译学的重要研究目标。经验科学中感性常常僭越知性,本体能起到限定界限的作用,划定知性范畴的运用界限。在哲学本体论中,本体、本质和现象皆是认识的出发点,决定和指导认识方法,本体与实在有关,现象是相对的、个体的、片段的经验,本质是真实的、绝对的、整体的经验。现象多面,本质唯一。进而言之,经验世界的现象是个体多样的经验,但本质是对本体的拷问。故此,翻译学终需回归和追问翻译本质。
翻译本质与“实践”“经历”等行为或事件直接相关。翻译行为是翻译学*核心的研究对象。汉语中,“翻译”之“翻”仅为摹状,“译”为“翻译”之本。作为人类交流行为,“译”在翻译行为及其译学研究坐标系中处于原点位置,如图1-1所示(黄忠廉,2015)。“译”即“易”,后者本意“熔锡铸器”,有“变化”和“改换”之意。探究翻译,旨在明了其中的“变化”与“改换”,而“变通”与“转化”为“变”之本,翻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内蕴于翻译的“变通”与“转化”,即翻译行为。根据上述本体论分析,获得关于翻译*真实的、绝对的、整体的经验理解和认识翻译行为为基础,以此为获得关于翻译正确知识之途径。
图1-1 翻译在译学研究坐标中的定位
1.3.2 翻译本质应是当今翻译学的重要对象
作为经验科学,翻译学的一切证据皆来自经验世界中的翻译问题。若没有对核心研究问题的把控,科学方法所得的普遍性知识并不能完全推动学科的进步,毕竟“不同学科是为解释各种现象而划分”(奥卡沙,2009:55)。果如上文所析,翻译之本是“译”,译之核心是“变通”与“转化”,译学理论则需解释“变通”与“转化”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并对经验世界的变通和转化进行预测。这一现实需求从国家层面也可得到明证,比如2016年、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为翻译学研究所定的唯一选题便是“双语对比与翻译转换研究”。
本体论亦可促建“翻译”研究关系树,形成“翻译”研究的关系网,其形如树。“翻译”是树干,其轴心是“变(通+转)化”,“翻译”可以顶天立地,其上,枝繁叶茂,上可产生翻译的思想、理论、学科等;其下,根系发达,下可深究翻译的几大要素及其关系等。根深才能叶茂,抓住了翻译的本质,才能一剑封喉,把握翻译学的本体。
1.3.3 元学科构建需要基于翻译本质
纵观科学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科学方法的应用,还同样依赖于系统性的理论和明确的问题研究。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对翻译学本体研究的元学科反思显然是理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姆斯1972年的宣言将翻译学研究对象界定为“翻译现象”,进而将学科目标设为“描述关于特殊现象的经验,建立解释和预测现象的原则”(Holmes,1988:75)。以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学科目标定为“关注译本生成和译本描述过程的问题 创立一套能用作译本生成指导原则的综合理论”(Lefevere,1978:234-235)。在他看来,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译本生成和译本描述过程的问题”。诚然,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翻译研究者理论上属于同一科学共同体,共享一系列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比较霍姆斯与勒菲弗尔关于翻译学的描述,二者似乎并未就研究对象达成共识。
霍姆斯宣言发表50年以来,翻译研究无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缺乏明晰研究对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德拉巴斯蒂塔曾用“充满讽刺性的矛盾”来形容翻译学研究对象的偏离:“翻译学的学科地位越牢固,翻译这一翻译学核心研究对象就越来越被消解。”(Delabastita,2003:9)毫无疑问,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但翻译本身是个多义词,其复杂性见于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