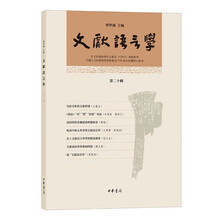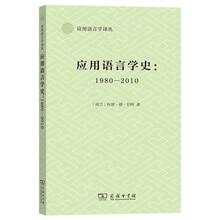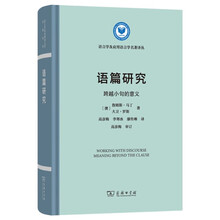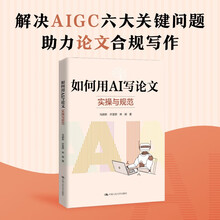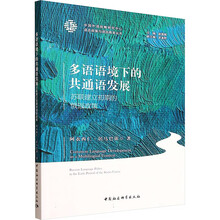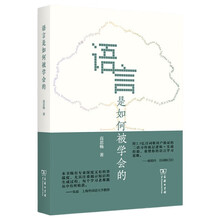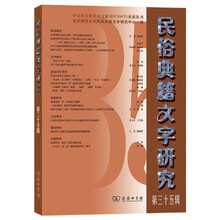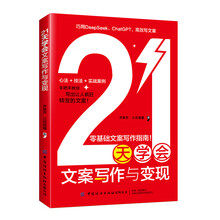绪论
第一节 术语翻译方法论研究概述
一、研究对象解析
“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使得自身获得发展与进步的功能活动的手段,包括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方法是关键。方法可使人类活动更加规范化、程式化、逻辑化,从而使人类活动达到预设目标。方法贯穿于理论与实践,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是其根本,因此,方法的研究与总结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方法“既包括认识方法、表达方法,也包括实践方法” ,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各门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如数学中的微分法、积分法),二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如数学方法、模型法),三是科学研究的哲学指导原则。” 方法有普遍与特殊之分、抽象与具体之分,更有适用领域的区别,各种方法并列,共同构筑起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与学说,“是以方法为实践基础,通过理论抽象而获得的有关方法知识体系的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①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②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前者指元方法论,是*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后者指具体科学方法论,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由此可见,方法论具有层次之分。对应方法的三个层次,方法论常被划分为:首先是比较具体的各专门学科的方法论;其次是概括科学研究一般方法的方法论,包括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或人文科学方法论;*后是从哲学认识论高度论述的更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即元方法论。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理论说明与逻辑抽象,是具体的、个别的方法的体系化与理论化,因此相对于方法而言,方法论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和统一性等特征。
翻译方法指译者根据一定的翻译任务和要求,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取的具体的途径、策略、方法和技巧,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翻译的总设想;二是解决翻译问题的具体方法。翻译方法可分为全译方法和变译方法。全译方法包括对译、增译、减译等;变译方法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等。翻译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它来自翻译实践又可指导翻译实践,“对翻译方法科学系统的认识,就是翻译方法论” ,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与翻译研究方法论。翻译实践方法论可划分为全译方法论和变译方法论;翻译研究方法论包含“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和从方法到学科的研究阶梯。
翻译方法论研究就是对翻译实践方法论与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探求和阐述。一方面,它应对翻译实践及研究方法论做出认识论的哲学分析;另一方面,它应阐述翻译各实践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特点、性质、作用、范围和局限,研究方法的发生、发展规律,讨论诸方法间的联系和区别,研究各方法的理论基础及运用方法时所应遵循的原则等。翻译方法论研究的目的正在于为人们实践和研究翻译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术语翻译方法论,是术语翻译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是翻译方法论在词级和语级语言单位上的演绎性体现。正因如此,以句群为操作单位的变译方法不适用于术语翻译,而术语翻译研究应遵循全译观。术语翻译方法论研究可具体化为术语全译方法论的研究及术语翻译研究方法论的研究。限于篇幅及笔者的能力和时间,本书将研究视野限定于术语全译方法论的研究,且着眼于英语术语的汉译,暂不将术语翻译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列入本书的讨论范围。
二、国内外术语翻译研究动态
术语翻译方法论研究主要指术语汉译方法论的阐述与说明,且集中于术语汉译这一单向翻译行为。综观世界翻译史,术语翻译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基于方法论是研究方法之本质与规律的学科体系这一论断,我们的文献综述以术语翻译方法为主,兼顾术语翻译的其他方面,主要是因为术语翻译方法的论述经常依附于术语翻译研究的其他方面,如术语翻译原则、术语翻译标准、译名标准化等。
(一)国内研究动态
目前国内翻译界公认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而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开展。每一次翻译高潮中都出现过关于术语翻译的宝贵思想,对今天的术语翻译研究大有裨益。依据收集到的相关文献,我们的综述起自三国,止于当今,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两个阶段,分别从术语翻译研究的不同角度进行。
1. 术语翻译的1980年前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译论中涉及术语翻译的主要是有关术语翻译方法、术语翻译原则、译名统一等方面的论述。
1)有关术语翻译方法的研究
开创中国译经史新风格的唐代名僧玄奘提出了“五不翻”原则,所谓的“不翻”即音译,这是有关术语翻译方法的*早论述。玄奘具体提出了五种不翻的情况,即“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 。这五种情况尽管并非全是指向佛教术语的翻译,但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术语零翻译 的使用条件。此外,玄奘还针对佛经术语翻译提出了“译名假借法”,即“玄奘有时候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 。宋初高僧赞宁主持编纂了一部《宋高僧传》,在此书中,赞宁总结了我国的佛经翻译史,讨论了翻译的性质和功能,并就佛经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六例”。其中,第一例为“译字译音”,即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 ,虽“六例”不是专门针对术语翻译提出的,但现今术语翻译所采用的音译、意译等方法,就是“译音、译字”演进的结果,其中,“译音不译字”为音译,“音字俱译”为意译。古代少数民族的某些翻译思想对术语翻译也有一定启示,如赤松德赞所提出的“翻译地方、动物、花卉、草木等名称”,“可以在所译名称前冠上‘地方’或‘花’等,表明是哪一种事物的名称,而保留梵文的原样”(即音译) ,这相当于我们今天进行术语翻译时常用的“音译加注”译法。徐光启创造性地用简练的中文对译术语,他与利玛窦创译的术语如“平行线”“三角形”等一直流传至今天;傅兰雅(John Fryer)在化学元素的翻译中创造了“借用偏僻汉字”和“创造易懂新字”的翻译方法;严复将术语的翻译方法分为“译”(译义)与“不译”(译音)两种,即“译者谓译其义,不译者则但传其音”,并强调对中文相类似语汇进行详细考察之后才能进行翻译;朱自清将历来名词的翻译方法概括为五种,即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造新字、造新义)、音译、意译。
2)有关术语翻译原则的研究
后秦僧人鸠摩罗什*早提及了佛教术语的翻译原则,他主张创立佛经专用名词或者采用音译名词,力求统一译名,避免一词多译。明末西学翻译家李之藻广译西书,其*有影响的译著是与利玛窦合译的《园容较义》《同文算指》,他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其中包括创译术语,强调“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坚持“辞能达意”的原则,他所创译的不少术语译名沿用至今。我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伯承规定了军事术语翻译的三项原则:根据内涵正确命名、表达清晰不能混淆、沿用军语使之统一。周作人提出了译名的音译原则,其中音译“名从主人”原则被后人广泛接受。杨惟义提出昆虫学名的翻译及其译名应统一坚持以下原则:竭力采用中国固有名词;如无固有名词,则采用土名;若无古名及土名,则可译义;如遇地名、人名或其他原意难以查悉的学名,尽可仅译其音,而加以虫字旁。著名作家老舍认为科学、哲学名词的翻译应该“既信且俗”,反对“生硬难解”,现今的术语翻译仍应遵循这一原则。
3)有关译名的研究
中国自古就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语言文字的统一与规范是国家强盛、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与重要象征。译名可指术语译名,也可指非术语译名,但对非术语译名的讨论定会对术语翻译有所启示,因此,下文综述已包含非术语译名。
*早讨论译名问题的是后秦的僧睿,他指出,译名问题在佛经翻译中意义重大,如名实不符,那么读者对所译经文的理解将南辕北辙,越钻研离原意越远,因此译者应详细地理解原意,反复考虑汉译名是否对等,然后才能正确定名。傅兰雅,近代西学东渐的巨擘,始终致力于汉译术语译名的确立和统一,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探讨,他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将自己所使用的术语翻译原则总结为三条 ,其中设立新名的三法正是傅兰雅本人在翻译外国术语时一贯采用的描述法、音译法和描述音译相结合法;此外,他还引领益智书会 统一科学术语体系,着重探讨了化学术语的翻译问题。傅兰雅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所提出的术语翻译规则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后来术语体系确立的准则,对中国科技发展意义重大。梁启超对译名问题也进行过详尽切实的论述,“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或者参考日本译名,对于新出之物,“必以造新字(词)为第一义”,其目的是实现译名的统一。高凤谦的《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是近代译论史上的名篇,作者在其中提出了统一译名的问题,即“译书之要有二,一曰辨名物 一曰谐声音” ,前者为意译,后者为音译。著名政治家和大学者章士钊在其译论《论翻译名义》中就国外学术新词汇的正确译名问题发表了详尽的见解。他指出,“翻译西方重要新术语(如‘逻辑’),必须做到准确涵括其全部意义,如果‘意译’做不到这一点,则宁取音译” ,这一观点对今天的术语翻译仍有意义。近代教育家胡以鲁的《论译名》中论述了译名的“决以意译为原则”的道理,同时继承了玄奘“五不翻”的翻译理论,在当时的译名讨论文章中非同凡响。益智书会编译出版过很多科学教科书,并为编译教科书而从事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还针对术语的翻译与统一问题于1896年成立了科技术语委员会,负责统一术语译名,《协定化学名目》和《术语辞汇》是其统一科技术语的两项主要成果,后者汇集了当时常见科技术语的各种译法,强调化学名词的意译原则,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1919年前后,研究科学名词统一之风大盛。陈独秀于1916年发表了《西文译音私议》,探讨了西方主要语言的译名问题,他指出:“译西籍,方舆姓氏、权衡度量、言人人殊。逐物定名,将繁无限纪。今各就单音,拟以汉字。” 杰出的翻译理论家郑振铎在1921年6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要求统一文学名词译名。他认为,全部文学理论术语应该意译,而人名、地名及部分书名应该音译,这一观点后来为翻译界所普遍承认与采用。著名作家朱自清的精彩译论《译名》将历来的译名方法概括为五种,即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音译、义译,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提倡义译,同时也不简单地排斥音译和借用,对译名问题进行了比较辩证、公允的论述。1950年5月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抓译名统一工作。
通过对我国历史上有关术语译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术语翻译方法的讨论一般依附于术语翻译的相关方面,*明显的莫过于译名统一问题。译名问题贯穿我国译论史始终,许多学者从译名统一角度探讨了术语的译法。译名统一是目的,术语译法是手段,目的决定手段的选择毫无争议,但手段的改进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目的,即规范术语翻译方法是译名统一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也正是本书的出发点之一。
2. 术语翻译的1980年后文献综述
除黄忠廉和胡远兵 从文字学、语言学、术语学和翻译学角度出发提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