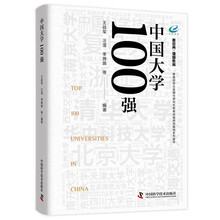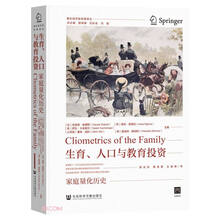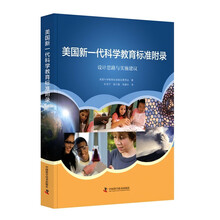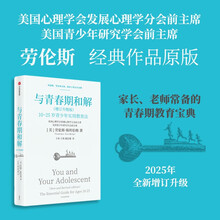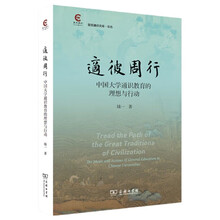**章中国义务教育研究的问题与认知
我国是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义务教育发展较为迅速和时空结构较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有丰富的义务教育地理资源,是开展义务教育地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较为理想和重要的天然实验室之一。对义务教育地理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义务教育的时空格局,促进教育地理学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丰富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和学科旨趣。同时,我国义务教育时空结构特别是区域差距的合理性问题日趋突出,在揭示我国义务教育时空格局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调控方案,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特征规定了义务教育的区域评估必须考虑民族区域这一因素,充分重视和系统考虑民族地理因素在义务教育时空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节中国义务教育研究的既有认知
目前,学界对中国义务教育地理的一系列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范式探索三个方面。其中,理论研究聚焦于教育地理学学科理论问题,实证研究侧重于义务教育的时空结构演变,范式探索则主要解决教育地理研究框架的建构问题。
一、理论研究:教育地理学学科理论研究进展
教育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在国外始于 1950年(Eisen,1951;McNee,1966;Ryba, 1968),20世纪 50—70年代的研究议题集中于多尺度、跨文化的教育现象分布和变异,以及教育空间扩散的地理因素、学校位置和教学区的确定等。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教育地理学的研究不断增多(罗明东, 2000,2001a,2001b, 2003)。从学科渊源的层面上看,国外 20世纪 50年代的学科建构和我国 20世纪 90年代的教育地理学的兴起主要是尝试从地理学中获得理解和研究教育地理问题的资源,注重对教育的空间进行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由于地理学家的参与,研究者更广泛地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教育的地理问题,出现了“教育社会地理”(social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Collins,Coleman,2008)、“教育情感地理”(geographies of emotion education)(Hemming,2007;Kenway,Youdell,2011)、“儿童地理”(children geographies)(Holloway et al.,2011)等议题,使地方与空间概念成为联结教育地理问题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桥梁,更注重教育的地方研究。2007年《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的专辑“教育地理”(Geographies of Education)(Butler,Hamnett,2007),2013年《加拿大地理学家》(The Canadian Geographer)的专辑“教育地理评论”(Critical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McCreary et al.,2013),以及主流地理学期刊《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Holloway et al.,2011)和《英国地理学家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Holloway,J.ns,2007;Kraftl,2013)所刊教育地理文章均反映了教育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议题和方法上的共振,可用“文化转向”“空间转向”“地方转向”来表达教育地理学研究旨趣的转变。教育学主流期刊《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Apple,2001;Brock, 2013a,2013b;Taylor et al.,2013)、《牛津教育评论》(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Taylor,2009)和《教育历史》(History of Education)(Burke,2010)等所刊教育地理学文章亦大致说明了如上转变趋势。
目前,约翰斯顿等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三版到第五版均有“教育地理学”词条( Johnston et al.,2006),国内出版的《地理学名词》中也有“教育地理学”词条(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07)。特别是比较教育学家尝试从比较教育中暗含的空间和地方层面上建构包括从个体到国际层面、从心理到客观世界、从个人微观关系到国际教育环境、从家庭到社会、从校内到校外的地理研究框架(Brock,1976,1984,1992,2010,2013a,2013b;Kraftl,2013;杨颖等, 2016;Taylor,2009;Taylor et al.,2013)。
二、实证研究:中国义务教育时空结构演变研究进展
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已从量的均衡转变为质的均衡(国家教育督导团, 2006, 2009;瞿瑛, 201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督导评估研究中心, 2010;于建福, 2002),构建适宜于评价我国义务教育空间均衡与公平的指标体系,研究我国义务教育在质上的均衡与未来发展,成为教育均衡研究的关键点(袁振国, 2003;翟博, 2006;彭世华等, 2012),并应在县域、市域、省域和国家层面上协同推进(***基础教育一司等, 2012a,2012b,2012c,2012d)。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空间均衡研究指标体系主要涉及入学率、经费投入、学校占地(建筑)面积、多媒体普及化程度、教师合格率(翟博, 2006;柳海民,杨兆山,2007;柳海民,周霖, 2007;楼世洲, 2012;傅禄建等, 2013)、教师学历结构(朱益明,贺绍禹, 2000;张谦舵, 2014)和要素的时空结构演变等。在研究类型上,主要包括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比较研究(张谦舵等, 2014a,2014c;潘玉君等,2014)、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比较研究(财政部教科文司等, 2005)、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均衡研究(校际研究,如安晓敏, 2012;市域研究,如卢晓旭等, 2010,2011;县域研究,如周守军, 2013;多尺度研究,如张珏,张振助, 2011;田芬, 2004;翟博, 2013;刘生旺,陈鑫, 2012;高庆彦, 2014)等。
在我国不同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态势的研究方面,成果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研究(王秀云,从春侠, 2001;王嘉毅,吕国光, 2006;杜育红, 2011;王根顺,饶慧, 2012),需要加强协同东、中、西部,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综合研究。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间或民族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对于我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凌,曹能秀, 2000)。但目前对义务教育时空结构演变的研究多集中于个别民族地区(特别地集中于云南省,冯春林,赵治国, 1995;常锡光, 2008;谢旭辉, 2009;马丽娟, 2009;普成林等, 2010;赵新国,毛晓玲, 2012;李官,王凌, 2013;刘芳,李劲松, 2013;李文钢, 2013;张谦舵, 2014;伍秋婵, 2014;彭义敏, 2014)或个别民族的研究(黄澄, 2008),也偶见区域协同关系研究的案例(成巧云,施涌, 2005)。因而,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急需加强研究的领域。关于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机制和对策方面,目前的研究注重挖掘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内容,以及教育基础设施和经济支持的保障(袁晓文, 2003;王嘉毅,吕国光, 2006;杨军, 2006;孟小军, 2007;田琳,于 布仁巴雅尔, 2008;王传三, 2008;刘明新, 2012;苏德, 2013)。
在教育地图研究和编制方面,目前主要有《中国教育地图集》(《中国教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中国教育地图集》(《中国教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9)、《北京教育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上海市教育地图集》(《上海市教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华地图学社, 2003)等。近年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的快速发展,关于教育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亦有了初步的案例性研究(赵芳等, 2011),但尚需要在区域层面、全国层面进行教育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三、范式探索:教育地理研究框架的建构
2000年至今,国内外学者系统地进行了以空间为核心的教育研究框架探索,这一框架能为义务教育地理的研究框架的确定提供支撑,但对于义务教育的空间问题,亦当探索其特殊性。总体而言,当前教育地理已建构起了从全球、区域、国家、省区、社区到个体的空间尺度研究框架( Brock,2013a,2013b),概而言之,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尺度。
微观研究能够在学习者、学习空间、学校与社区的地理研究中观察到。微观研究成为近年来教育研究的主要导向之一,地理学方面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with IBG)]的“儿童地理学”工作组关注儿童入学中的地域身份选择以及学校中的身份认同( Reay,2007;Vanderbeck,2005),即教育活动中的心理地理。学习空间方面的研究关注学生活动的特殊空间构造(或称“隐藏地理”,hidden geographies),比如,学校中的种族空间(Valentine et al.,2002)、吸烟区( Collins,2006)、宗教空间( Valentine et al.,2002),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群体排斥( Thomas,2005)。值得注意的是,学习空间的含义正在泛化,家、托儿所、课外俱乐部等场所亦被认为是与正式教育直接相关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具有众源、伸展、渗透三种空间特征,对学习者的身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Duncan, Smith,2002;Holloway,1998;Kraftl,2013;Smith,Barker,2004)。学校与社区的研究关注影响特殊学校空间特征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种族、民族、收入差异、职业差异等造成的学生生源的差异及其缔造的特殊社区景观,如士绅化这种典型的学区景观( Witten et al.,2001;Lees et al.,2007;Smith,2008)。
中观尺度主要包括区域和国家,区域尺度上的研究以地方***门的政策地理为主要关注点。有研究者通过研究 4个不同地方教育局的规模、政策管理、位置和历史,探究了权力分配改变后学校和地方教育局之间出现的新关系形式以及地方教育局新的组织文化和实践( Radnor,Ball,1996)。研究发现,当前地方教育局与学校呈现多样的“合作关系”,这与地方***门的政策管理和历史、组织文化和规模相关。 Johnston等( 2006)研究了英格兰学校的种族隔离程度,分析了这一隔离是否比居住地隔离程度更高。研究表明,比起邻里间种族隔离的程度,学校的隔离程度更高,尤其是在小学和有种族群体的学校,影响种族隔离程度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政策。这是一项区域性层次的比较研究,并且包含了农村和城市的变化。基于地方尺度的成绩差异研究,例如, Byrne和 Williamson(1971)研究了地方教育局的政策对教育成绩的影响,认为在教育社会学中地方政策的影响被忽视,政策这一变量对教育成绩有决定作用,对地方教育政策类型的追踪可以解释教育成就的多样模式。在地方性质的学校(学区)内,影响学习方式的主要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及教师之间的协作方式,学校间学习网络的发展、教学与学习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Lee et al.,2012)。Taylor(2001)研究了英格兰新教育市场选择的多样化地理影响因素,通过学校供给多样化和家长选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