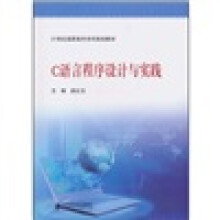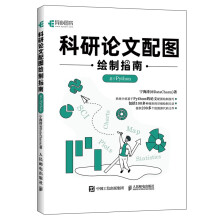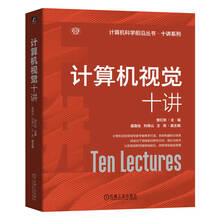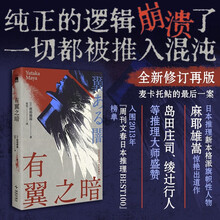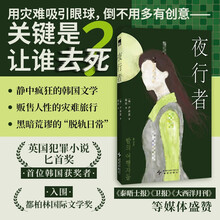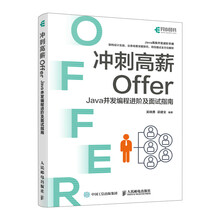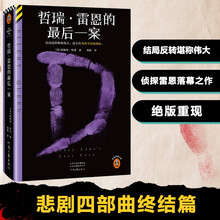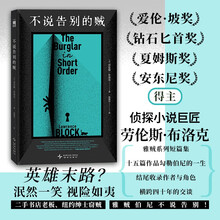开篇
第1章 导言
1.1 本书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的农业经营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了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性,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并从“统”和“分”两个层次提出了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两个转变”的政策要求。在“统”的层次上,《决定》提出:“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在“分”的层次上,《决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特别是重点培养种养业能人大户,通过他们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示范户和“领头雁”。
农民合作社(简称合作社) 是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农户分散经营具有制度上的潜在优势,这一点在理论或经验上都不太难找到有力的支持证据。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合作社能够通过成员之间的合作实现外部交易的内在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合作社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单个农户与外部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整合,通过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实现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合作社通过成员合作可以实现农户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以获取规模经济,或者因为通过合作可以提高市场谈判地位和能力,对抗垄断,或者因为通过集体投资可以实现新技术引进和技术、产品创新来谋求超额利润。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地区,合作社多运行良好,为各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USDA,2013;Filippi,2012;Bijman et al.,2012)。许多国家经验表明,合作社对于促进就业、益贫增长与社会和谐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合作社在减少技术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联结小农户与现代市场、改善农民生活方式、完善乡村治理等方面也发挥了公司等其他组织无可比拟的优势(Zhou et al.,2016;Naziri et al.,2014;Valentinov,2007;Herbst and Prüfer,2007;Tripathi et al.,2005;LeVay,1983;周洁红等,2019;周文灿,2015;钟真和孔祥智,2012)。北美、北欧和日本等地区(国家)农业发展过程中合作社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福利改善发挥的积极作用也验证了合作社的价值(周应恒等,2013;黄祖辉和梁巧,2007)。
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均分土地制度决定了中国全局性的小农经营特点,并使中国“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破局异常艰难。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小农户”经营,因此,中国的农业经济也被称为小农经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农地均分制度对中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减少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对农民增收的制约也日益明显。小农经营不仅制约农户采用机械化和新技术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农技推广、小农与现代市场融合的难度和成本(黄季焜等,2008)。此外,小农家庭经营具有自产自用的组织特点,即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会因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持续投入劳力,直到边际报酬下降到近于零。因此,尽管小家庭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可能高于经营式农场,但劳动生产率则要低于经营式农场(黄宗智,2010),这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提升的可能性。而且,随着中国小农户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开放、流动、分工、社会化的大市场中,小农在规模、信息、资金、技术和抗风险等方面的弱势位置,决定了他们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利益分享、抵御外部市场冲击,以及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等多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身陷诸多困境,这些挑战和困境要求小农在竞争中必须扬长避短,通过发展自身能力和提高组织化程度来谋求生存状况的改善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白军飞等,2014)。
合作社相对农户分散经营的潜在优势,以及中国小农分散经营对农业生产日益凸显的不利影响和小农在参与现代大市场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与面临的困境,促成了2007年后中国政府对合作社发展的大力支持。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简称《合作社法》)的颁布和实施,我国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对合作社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扶持。在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发展迅速,合作社数量和成员数量都有飞跃式增长。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合作社有153.1万家,每个行政村拥有2家以上合作社,入社农户10 090万户,覆盖了全国42%的农户。“十二五”期间,合作社数量增长近3倍,农户入社率提高近31个百分点。 然而,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的合作社在实践中却极少能够遵循经典的制度安排,它们在两方面的表现普遍不太理想:一是合作社服务功能较为薄弱(黄季焜等,2010),各项服务功能提供比例都较低,对成员影响有限;二是即便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功能,在盈余分配环节也很少会实行按交易量返还(应瑞瑶等,2016)。
在经历《合作社法》出台后的这轮数量增长式发展后,中国合作社发展质量和不规范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提醒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开始反思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前景和策略及相关理论问题(徐旭初,2013)。事实上,关于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成效和功过得失,学界和政界人士自《合作社法》出台两三年后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持非常肯定的观点,有的持非常消极的观点。持肯定观点的一方认为,中国合作社发展成效显著,虽然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总体上中国合作社发展迅速,在提升农户生产组织化水平上已发挥积极作用(陈富桥等,2013;伊藤顺一等,2011;蔡荣,2011;邓宏图和崔宝敏,2008;黄祖辉和梁巧,2007)。这种支持的观点主要来自官方的报告、一些针对成功合作社的案例研究,以及少数基于特定合作社个案对成员影响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合作社发展的成绩和问题,接受合作社发展初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后续再逐步规范。然而持消极观点的一方则认为,合作社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暴露的问题远远超过成绩(徐健和汪旭晖,2009)。由成员自己组建的合作社较少,普遍存在以合作社名义套取政策资源的现象,合作社民主治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形同虚设,合作社“名实不符”“有名无实”“假合作社”“翻牌合作社”“精英俘获”“大农吃小农”“农户被参与”等问题严重,这迫使许多学者开始深刻反思我国合作社发展的策略和成效(邓衡山和王文烂,2014;潘劲,2011;崔宝玉和陈强,2011),甚至质疑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合作社。
中国合作社发展走到了迫切需要进行系统总结和理性反思的十字路口。关于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有若干重要问题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扎实的实证分析进行深入研究来予以解答,从而为我国合作社未来的发展前景、方向和政策优化提供建设性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第一组问题:中国合作社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对农民生产和收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农民参与程度怎样?存在哪些问题?
虽然合作社在过去多年被视为解决我国小农困境的重要策略,也被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虽然关于合作社发展成效的争议如此激烈,但现有研究和文献对于合作社发展状况与成效的判断和分析因为所依据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导致结论的一般性和严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现有研判合作社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