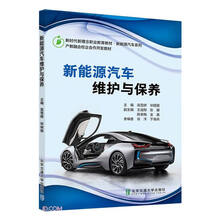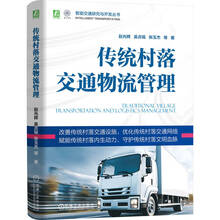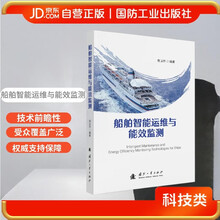第1章绪论
1.1研究概述
1.1.1研究背景
1.1.1.1现实背景
(1)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被置于新发展理念的*位。
创新驱动发展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国家发展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优势,我国走出了一条要素驱动的发展之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国内要素成本价格提高、环境持续恶化,传统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创新成为新形势下破解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特别是科技创新,由于当前国际竞争主要以科技竞赛等形式上演,只有国家取得了科学技术领域的先进地位,才能避免受制于人。同时,科技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带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关键内生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任务,其中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是国家从空间视角出发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聚焦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整体提升”,指明了优化区域创新布局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思路。
所谓“优化区域创新布局”,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要从全局角度分析掌握不同地区的创新发展水平和地区之间的创新关系,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创新要素集聚和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想要整体提升,仅靠部分科技发达地区的创新带动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在于由点到轴再到面,形成创新城市合理布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创新网络系统。二是,强调地区间协同创新,通过深化合作、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效率。创新是知识流动与创造的过程,只有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在地区间充分流动,带动知识和技术不断碰撞融合,才更有可能发明和创造新的科学技术。三是,强调地区间合理分工,在不同区域尺度上实现创新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一部机器只有不同零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正常运转。同理,一个国家只有不同地区充分发挥各自专业化特长,形成一定区域范围内创新领域的多元化分工,才能真正从创新大国发展成为创新强国。
(2)高速铁路网络承载各类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正在重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建设交通强国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先行领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作为现代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速铁路具有速度快、节能环保、安全舒适、载客量大等优势。21世纪以来,我国高速铁路网络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2008~2019年,我国高速铁路客运量从734万人次/年增长至22.9亿人次/年,截至2020年末,我国高速铁路里程已达到3.8万km,高居世界**位。
有别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高速铁路以载人为主,几乎不提供货运功能。然而,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的主体,高速铁路搭载人口进行城际流动的同时,资本、信息、知识和技术等要素也随之频繁移动,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得到重塑。此外,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高速铁路能够影响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区位选择,改变人口和劳动力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市场规模和经济潜力,重构产业生产与商业服务等经济活动的地理格局。
高速铁路的一个特点是网络化。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年版),我国高速铁路网络在原“四纵四横”基础上,逐步建设形成“八纵八横”的主骨架网络。随着高速铁路网络越织越密,区域资源要素流动愈加频繁,国家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格局将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网络化将导致非线性变化。一条新高速铁路线路的开通对城市可达性、城市间连通性乃至网络整体密度的影响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加一,而可能是成倍甚至几何式的增长。另一方面,网络化将导致非均等变化。对于同处在高速铁路网络中的不同城市,由于各自网络位置不同,其受到网络发展演化的影响也将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想要全面掌握高速铁路网络的经济地理重塑作用,必须对高速铁路网络从无到有、从形成到发展的连续过程展开综合分析和系统研判。
(3)科学规划交通网络,推动经济社会活动合理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图上将黑龙江省瑷珲县(现黑河市)与云南省腾冲县(现腾冲市)相连,以此划分中国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这条连线的东南部,约占全国36%的土地上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而这条连线的西北部,约占全国64%的土地上仅居住着全国4%的人口。“胡焕庸线”反映了20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不平衡现象,时至今日,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2018年11月18日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分化现象逐渐显现,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区域发展机制还不完善,难以适应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目标。
“要想富,先修路”。我国一直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带动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交通系统的完善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都市圈、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系统提高了地区综合承载能力,有助于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但是也需要看到,交通基础设施在带来极大正外部性的同时,也面临着较高的投资回报压力。以高速铁路为例,高速铁路建设投资大、运营成本高,平均每千米高速铁路线路建设成本为8000万~1.2亿元(欧杰等,2016),目前国内多数高速铁路线路盈利能力仍然有限。仅从财务角度分析必然会低估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是提高交通网络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之与国家经济发展布局相适应,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财务负担和投资风险,还能够有效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集聚,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1.1.1.2理论背景
(1)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阐明商品运输成本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影响,但关于高速铁路等载人交通运输方式对创新地理的重塑效应分析不足。
近几十年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区域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著名的核心—边缘模型中,克鲁格曼指出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商品运输成本是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因素(Krugman,1991)。相较于其他传统运输方式,高速铁路虽然几乎不具备货物运输功能,但是却可以以更高的效率和速度承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跨区域流动,因此也能够给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目前,学者们已经对高速铁路的区域经济社会效应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但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学界关于高速铁路引起的均衡与极化效应尚未达成共识。虽然新经济地理学指出商品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呈“倒U形”关系,但由于高速铁路主要提供客运功能,几乎不具备货运能力,所以无法将核心—边缘模型对交通和产业集聚的分析结果直接应用于高速铁路。另一方面,至今仍缺少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系统归纳高速铁路对创新地理的综合效应及作用机制。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商品运输成本角度分析交通对经济和产业集聚的影响,关于高速铁路等载人交通运输方式对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的作用分析不足,相关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仍有待补充与完善。
(2)邻近动力学
邻近动力学派指出,地理邻近对创新网络形成的决定作用,为高速铁路的创新地理重塑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在实证研究层面,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仍然有限。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单一个体越来越难以高效率地完成复杂的创新任务,以多元主体相互合作和优势互补为基础,从而实现“1+1>2”效果的协同创新逐渐发展成为创新的重要模式。在演化经济地理学领域,以Boschma(2005)为代表的邻近动力学派提出多维邻近性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认知邻近(cognitive proximity)、组织邻近(organizational proximity)、社会邻近(social proximity)、制度邻近(institutional proximity)和地理邻近(geographical proximity)对创新网络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
近年来,虽然不断有研究从地理邻近性角度分析和检验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但相关实证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多局限于对创新产出水平的分析上,包括测度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和城市间合作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而关于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内容及区域创新分工的作用研究不足。另一方面,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多局限于对创新要素的分析上,包括识别高速铁路对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流动与集聚的影响,而关于高速铁路对创新主体的空间重分布效应研究不足。
(3)“流空间”理论
流空间重构传统地理时空思维,网络化为创新地理学以及高速铁路网络效应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
1989年,Castells*次提出“流空间”概念,旨在强调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发展,传统地理时空思维将得到重构,即由静态的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向流动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转变(Castells,1989)。同样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高速铁路虽然无法像ICT一样能够使多种“流”进行瞬间的移动,但从运输效率和运行速度角度评价,其相较于传统交通运输方式也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随着高速铁路每天承载大量的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区域间频繁快速移动,流空间将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空间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空间逻辑(孙中伟和路紫,2005)。
在Castells的理论体系中,“流”的概念和“网络”的概念相互交织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网络由一系列节点或中心被各种类型的流连接在一起所形成,而流空间是一种由不同类型的流占据支配地位的网络空间形态,包括知识流、技术流、资金流等。相较于传统的场所空间思维,流空间更加关注网络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从网络演化视角分析区域空间形态的发展过程。创新地理学恰好是一门研究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空间流动与集聚的学科(甄峰等,2001),但是目前关于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多围绕高速铁路的开通效应展开。因此,流空间思想和网络分析方法能够为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的网络效应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方法和技术支撑。
1.1.2研究问题
*先,本研究特别强调“网络”一词,旨在表明研究注重分析高速铁路线路从无到有、从形成到发展的连续过程及其对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的动态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关于高速铁路连通地区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仅对高速铁路的“开通效应”进行识别,通过0/1赋值区分未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和已开通高速铁路的城市,但是却忽视了已开通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