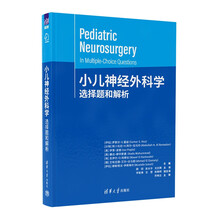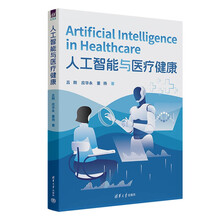1. 执业四十多年、检验超过2.3万具尸体的传奇法医,揭开职业生涯中未曾披露的案件真相。死因不明的婴儿,疑似自杀的少年情侣,离奇死亡的政府雇员……法医谢泼德满怀对生命的敬重和对真相的执着,详述曲折破案过程,记录普通人的生死悲欢。
2. 我们一生中可能遭遇的生命风险,这次就请法医谢泼德一次说清。为什么婴儿诞生后的第一年是最危险的?为什么而立之年的冒险行为往往会致死?杀死老年人的除了疾病,还有哪些因素?作者从法医病理学的角度,结合统计数据与真实案件,层层拆解人体的精巧构造,清晰解释各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隐患与主要死因。
3. 每一章犹如英式侦探剧,熟悉的暗黑反转与犀利吐槽!悬念感拉满,读者没有翻到最后一页,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4. 简体中文版采用精装双封,“多巴胺风”装帧设计斑斓绚丽,内封特别使用“无色压凹”工艺,专属彩蛋等待读者解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