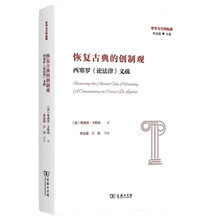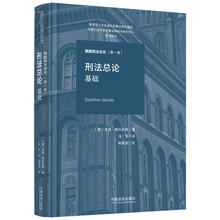立法政治说到底是组织政治。那些举足轻重的人聚在一起游说立法机关,让其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以及不想做什么。这种游说过程让立法者知道,如果他们通过一项特定法案,他们可能会结交哪些朋友或树了哪些敌人。因此,无组织的大众有时只能坐以待毙。这就是当人们谈到“特殊利益集团”胜出时的意思。
在警察执法方面,最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是警察本身,以及他们的近亲——检察官。警察工会的势力尤其强大。一旦推出了影响警察执法的法律,这些组织就会闻风而动。检察官和警官要么去敲议员们的家门,要么在立法听证会上作证。他们游说的目标是让他们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更多的权力和更少的监管。从警察和检察官一贯的为了完成任务而不顾一切的角度来看,只有从这方面理解才说得通。
另一方面,受警察执法影响的人通常组织性不高,甚至根本没有组织。强势的警察执法总是把最沉重的负担不分比例地压在少数族裔和不太富裕的人的肩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些被压迫的人不断地在立法过程中进行抗争。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你可能会想,“发生在卡尔沃身上的事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完全有可能。但问题是我们往往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去想这件事,但到那时却为时已晚了。
大多数人对警察执法的担忧,通常是一种会成为犯罪受害者的普遍担忧。在过去大约50年的时间里——即使是在犯罪率下降的时候——美国政治的噩梦一直是违法犯罪以及对犯罪的恐惧。因此,立法者通过“严厉打击犯罪”、实行“零容忍”和颁布类似“三振出局”等法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确保了自己的连任。
鉴于整个社会对犯罪的恐惧,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立法者不愿意采取措施来束缚警察的手脚。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人愿意在竞选时被竞争对手宣扬说他们对违法犯罪态度软弱。如果立法者制定制度来规范警察——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然后出了差错,他们就会被指控最近发生的恐怖犯罪是他们的错。
在房子被突袭搜查之后,沙伊·卡尔沃实际上设法通过了最温和的警察条例;吸取教训使这条法律得以通过。卡尔沃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与立法程序打交道,他认为一个好的起点应该是制定一部法律,规定警方报告特警队行动的频率。也许,如果这些信息得以公开,那么特警队的过度使用就会得到控制,或者人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但即使是这一小步也需要策驽砺钝,不懈努力;执法部门竭尽全力打压它。刑事司法政策基金会的负责人埃里克·斯特林指出:“袭击市长、杀死他的狗,以及其他完全无辜的白人,促成一次相对较小的立法行为……执法部门对此有一个非常坚决的、下意识的反对。”“那项法律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它于2014年到期,没有续期。”显然,让马里兰州的执法人员追踪发生了多少次特警突袭,实在是太过分了。
有些人不以为然,忽视对警察执法的立法,辩称这个体系中存在问责制。许多治安官参加选举。市长或市议会可以让警察局长离职。联邦调查局局长服从总统的意愿。这个观点似乎是说,如果警察执法出了问题,这些警官就会失业。
但事实上,这种选举问责制只会加剧问题的恶化。如果整个社会对犯罪猖獗现象过于焦虑,民选官员是其首当其冲的针对目标。如果犯罪率上升,选民就会愤怒,市长或其他当选官员就会发现自己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因此,市长们明智地把打击犯罪作为自己的职责,这样的话,只要事实如此,警方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执法自由。
要求市长对警察采取强硬措施的人寥寥无几。2013年,比尔·德布拉西奥当选为纽约市长,这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警察执法的选举,尤其是对有色人种进行拦停和搜查。但是你认为选举候选人有几次会与强势的警察对着干?即使是在纽约,媒体也花了数年时间监督纽约警察局的做法,才达到目前的水平。作为市长,德布拉西奥仍然需要警察。在他当选一年后,全国上下都看到了电视画面上的一排排警察默默转身背向市长,以示强烈不满,他不得不努力寻求弥补措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