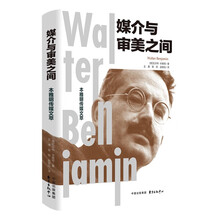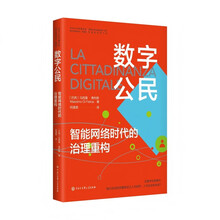在国内方面,国家必须得面对其行政和政治操作空间的减小,以及不同政党纲领的日益趋同现象所透出来的议会的某种惯性。
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取得成功之时,平民阶层遭受了社会创伤。我们因而看到了一个“三分之二社会”的轮廓:某种社会性掠夺建立了一种总体上看似乎只有三分之二人口受益的社会制度。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被牺牲掉了,慢慢地被抛弃到次等公民的阶层。政党丧失了公信力,而公众的政治参与度下降。回想起来,当年里根实际上只获得了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就当选总统了。在这种情形下,权力成为消极抗议的对象。这种消极的程度是三十年以来公共领域中前所未见的。
随着传媒越来越多地接受商业逻辑,我们可以观察到,根据人口特征以及消费能力划分受众的计划已在逐步实施之中。记者今后将分别针对根据市场策略建立起来的各个目标受众群,来从事新闻报道。这个过程肯定复杂,但总的来说,它以重现上面所言及的阶级的极化为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说,高品质的传媒以及那些自诩创建国家论坛的人(一如前欧洲公共服务机构)已经普遍减少。
对于美国的广播新闻来说,主动调整为特定的受众量身定做信息的行为尤其明显。这种做法在电视和报章杂志上也很突出。新一代读者文学涵养的滑坡对美国报章杂志的质量造成了深度的损害,这种滑坡的后果影响了整个行业。一些新的举措给人带来了扭转新闻碎片化趋势的印象。我们因此也可以论及美国一家新型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的成功。但是,这种创新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对于国家政治而言,整个可以维持的公共空间的式微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民族国家的危机、议会辩论的疲惫感和公众分裂化的交叉路口,反倒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繁花似锦、生机勃勃。这些运动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领域:环境、裁军、妇女的社会生存条件和法律权利、性少数群体、种族和少数族裔群体,以及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问题诸领域。
这些运动既没有相同的指向,也没有相同的目标和策略。更有甚者,它们其中的一些运动的参与者很快又分裂成为敌对的派别。然而,尽管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在兴趣方面颇有差异,例如女权主义运动和环保主义运动,但他们却不时地将各自的力量成功地联合起来,从事一些共同的活动。拉克劳(Laclau)和穆菲(Mouffe)合作完成的学术著作注意到这些运动带有“后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化倾向。①
虽然这些运动大多属于进步的类型,但也有的属于保守的或反动的类型,例如美国基督教运动的各种右翼人士,或在欧洲出现的反对移民的种族歧视团体。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激进主义的背景,通常都来自中产阶级,而且他们并不具备绝对的一致性。他们的政治基础不在已经建立的政党之内,尽管他们有时可能会与既有的政党,或者与更为传统的阶级组织(如各种工会)缔结短暂的联盟。
这些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参与者往往把日常生活的经验,特别是私人领域(如学校、街区等)的经验,转化为政治干预的规范性愿景。他们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他们可以用公道的价格获得信息与传播技术。得益于台式电脑、打印机和传真机的襄助,他们成功地承担了组织、传递信息和辩论等多重任务。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信息简报如今已能成为一个有效而便利的传通介质。信息简报、广告散页和报纸之间的分界变得模糊不清。此外,著作手稿提交之后的第二周就有可能成书的现象,亦已使新闻和出版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不再清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