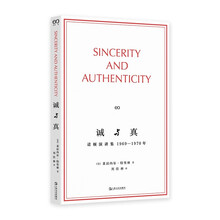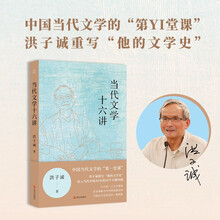我童年时期的大量阅读提供了可能,比如我最初对于《三国演义》的阅读就来源一整套“小人书”。我对“小人书”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到中学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的热潮,国家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古典白话小说《水浒全传》,这是我最早接触的真正的文学名著原本。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学校与家庭为我亲近自然创造了机会。当时学校的课业并不繁重,有大量时间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比如割青草、积肥来支援农村建设。当然,一方面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但另一方面,这些田间活动包括捕鱼、拾柴等,也给了当时的孩子们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培养出了一种生活趣味和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的童年时代并没有动漫和电视,但这种“与自然共生”的状态,经历时间的沉淀之后就能慢慢体现出对一个人成长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可能是当下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稀缺的部分。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一辈曾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校的中文系毕业生,也曾经从事文学研究并著书立说,他撰写的专著中还包括中国诗歌史,这与我的文学研究似乎存在着某种共鸣与交集。后来,我还曾在胡风办的《七月》杂志上看到祖父著作的广告。如果据此追溯,可以认为我选择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潜在的遗传基因。不过我的祖父在1948年前后就迁至台湾,而将我的父亲、祖母等留在了大陆,从此断了音讯,我获悉他的这些信息,也是在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这种“遗传”的追溯更近于一种自我想象或说精神上的自我连接吧!(2017-20,第17-18页)
“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我诞生在四川东部一个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出生的这个地方在那些时候是多么的热闹,坦克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地行驶,军舰与货轮抢道,弹道划亮了山城的夜空。当然,童年还有过小伙伴的游戏,有过小河边的捕鱼,有过防空洞里的“历险”,有过小饭铺里二角一碗的大汤圆,家庭命运的苦涩混杂着一颗无知童心的默默的欢乐。但是没有书,没有唐诗宋词,没有《红楼梦》和《鲁迅全集》,尽管我那时是多么珍惜到手的每一本连环画,我苍白的童年只有二舅夏夜里的“西游记”故事还闪耀着“文化”奇异的光芒。(1995-Z,第291页)
我所谓的“荒芜”不是一个比喻,它是真实的感受。我这代人开始读书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我们国家无论是具有文学性的经典名著还是儿童读物的出版都是空缺的,那时候能出的都是适应国家政治形势的一些著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录、文件之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70年代的“评法批儒”后统一印刷的《水浒传》,在这前面都有毛主席、鲁迅评点的文字,所以这也不是作为文学经典面世的,而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出版的,它掀起了全国人民“评《水浒》”的高潮,可谓奇观。所以说,“荒芜”是真实的景观。在这个荒芜年代中,唯一的色彩就是连环画。连环画不是随时都有,当时我在重庆,一个书店里连环画也不过两三本,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会出现一本新的连环画,这就是文学荒芜年代唯一散发出魅力的图书。荒芜年代的连环画对我的精神影响,可能是今天的儿童看美术图书、看动漫没法比拟的。因为今天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你看美术图书也好,看动漫也好,那只是诸多可选择的对象之一;但在我们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连环画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它构成的魔力是极大的。每个月我父母都会给我买一本连环画,那一天就成了我最盼望的日子。(2015-2,第171-172页)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