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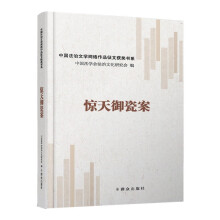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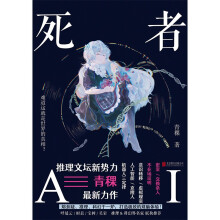



1. 名家名作。彼得 伯克经典的书籍史、文化史研究案例。
2. 视角独特。从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入手,不仅关注其内容,更关注其流传过程和读者人群。
3. 装帧精美。优雅设计加之贵族纸与牛津纸的搭配,便于携带。
第一章 传统与接受
在1724年出版的《廷臣》译本的献词中,罗伯特·杉伯(Robert Samber)写道:“《廷臣》如此之伟大,以至于其不能被仅仅局限于意大利的狭窄疆界之内……仅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宫廷所阅读、喜欢和赞美是不够的,为使大家更熟悉它,人们可以用每一个国家最为习惯的适当形式来装扮它。”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爵士曾以相似的方式评论道,“如果将不同国家”对卡斯蒂寥内的理想所表现出的各自特征“加以比较考察,那将是一项令人着魔的研究”。
本书试图对上述挑战做出回应。其首要目标是重构一项国际运动对地方和个人的含义,因而在回答广泛的一般性问题时,我们引入了目录学和社会学的细节研究方法。我将在尽量避免像其16世纪的一些编者那样将该对话的丰富内容归纳为简单的几方面的同时,重点介绍卡斯蒂寥内书中那些在大范围、长时间内吸引读者的内容,特别是其有关“优雅”(grace)和“从容”(sprezzatura)的讨论的部分。
在时间上,本书所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1528年《廷臣》出版后的第一个世纪,尽管其结尾部分将会讨论到晚近作品中对该文本的参考和引用。在空间上,我所关注的主要是欧洲,尽管偶尔也会涉及更广范围(从南亚次大陆到美洲大陆)的读者。在写作策略上,我更多关注的是意大利以外的读者。因为同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文化差别越大,对其著作积极接受的过程就越能被清楚地展现出来。尽管我最初并未打算对英国接受卡斯蒂寥内的情况给予特别关注,但我却发现我这样做了。我希望,这种从其内部对单一文化所做的认真研究,能多少减少一些存在于任何大范围的国际调查中的固有危险。
但一定的文化跨度又是必要的。因为我希望能够对人们理解“欧洲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of Europe)——换句话说,即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文化的逐渐整合——做出些许贡献。因此,我将尽量去考察《廷臣》之外的一些东西,将该文本作为一个研究案例来探讨三个在范围上更广的话题:意大利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对文艺复兴的接受、《廷臣》一书的历史,以及价值体系的历史。
对文艺复兴的接受
自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1860)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历史学家们已开始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对“自我”和“他者”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时代进行研究。布克哈特将这一新趋势的特点界定为“个体的发展”,并注意到了艺术家和作家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竞争与自觉,如他们的自画像和自传中所显示出的那样。
最近,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仿效诸如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其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现”的研究等研究方法,人们开始从其自我展现(self presentation)、自我塑造(self fashioning或selbststilisierung)的视角对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皇帝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等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进行研究。这些对当时主要人物的研究引发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他们的领导在当时是否得到了广泛的追随。由于卡斯蒂寥内的对话看上去非常像是一部指导个人进行自我塑造的指南,因此,不单在意大利而且在国外,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廷臣》的反应进行考察或许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种对反应进行研究的视角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对文艺复兴运动传播的传统叙述经常将之描述为欧洲范围内的一路凯歌,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相继屈服于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皮科·德拉·米朗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阿里奥斯托(Ariosto)、马基雅维里和其他主要艺术家、作家与思想家的魅力。
此类解释存在两个根本的弱点。第一个弱点是,人们设想此时只有意大利人是积极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而其他欧洲人则是被动的,仅仅是“影响”(influence,一个经常为思想史家们[intellectual historian]毫不批判地加以使用的、起源于占星学的词汇)的接受者。15世纪时一些意大利人对来自荷兰的绘画作品所表现出的兴趣告诉我们,他们至少已经注意到了国外艺术家的创造性。
传统叙述关于文艺复兴运动传播的第二个弱点是将所“接受的”与所“给予的”视为同一。尽管“传统”(tradition)一词的原意是“传下来”(handing down),但我们却很难否认概念、习惯和价值体系在被传播过程中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为适应新的空间或时间环境,传统经常会被改造、重新解释或重建——不管这种重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例如,古典传统在中世纪即以这种方式被重建。阿喀琉斯等荷马时代的英雄被改造成骑士,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则变成了巫师,朱庇特(Jupiter)(有时)被当成学者,墨丘利(Mercury)被当成主教,等等。
如果将视角从传统转移到个人身上,我们将经常发现他们在进行某种“修补术”,即从他们身边的文化中选取任何吸引他们、与他们相关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他们已拥有的知识将之同化。虽然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为外来事物所吸引,但他们都会经过一个对新事物进行重新解释和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从而将他们的发现自我内化。4换句话说,读者、听众和观众是积极的接受者和改造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他们对新事物的占有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其自身的逻辑。这种占有的逻辑经常被某一社会群体所分享,因此,这类社会群体可以被形容为“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或有时为“文本共同体”(textual community)。在这种共同体中,某一本书会被用来作为其成员思考和行动的指南。尽管有关共同体的此类概念会产生误导性影响,但我们却仍然无法离开它们。尽管它们具有导致我们忘记观点上的个体差异或将之最小化的危险,但在使我们记起所被分享之物方面它们却是不可或缺的。
不断进行重新解释和再情境化的过程,一方面侵蚀着传统,一方面却又通过确保其继续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而得以保存下来。如这一渐进的重新解释过程因某些原因被阻断,那么,一种要求进行更加激进的变革(change)或“改革”(reform)的压力将会形成。例如,我们称之为“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文化运动,即是对基督教传统进行激进的重新解释的一个生动例证。
根据上文所陈述的观点,我们认为,有关“发明”(invention)和“传播”(diffusion)之间的习惯性区分应当被看作一种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应是一种性质上的差别——为了支持这一观点,需要写一本比本书更厚的书。最好的做法,是将发明本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改造过程,例如:印刷机的发明是对葡萄榨汁机(wine press)的创造性改造,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出现是对史诗的创造性改编,等等。
因此,对文艺复兴运动而言,有益的做法是:抛弃仅将之看作产生于佛罗伦萨的新观念和新形象(image)对外界产生“影响”或“传播”的观念,而代之以追问,从哥特式建筑到经院哲学,意大利对欧洲其他地区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有什么“影响”?他们接受这些 “影响”的逻辑是什么?意大利人的新礼仪或新观念为什么会被融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固有传统之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研究接受者们是如何对他们所看到、听到或读到的东西进行解释的。我们必须关注他们感性的“图式”(perceptual ‘schemata’)。我们必须关心日渐为文艺理论家们所称为他们的“期望地平线”(horizons of expectation)的东西。
简而言之,文化史学家通过吸收仍多少带有外来色彩的 “接受”的概念,并将之用来修改有关传统的传统观念,将会有所收获。事实上,如果不是作为一个概念的话,这个词语对学习和研究文艺复兴的学生来说应当是相当熟悉的,因为接受(Rezeption)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即已被用来描绘人文主义和罗马法的传播了。无论如何,文艺复兴中有关文学模仿(literary imitation)(见下文第81—82页)的性质的争论,被认为是有关传统与创新之间兼容性的接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有关文本被接受情况的研究将会带来一些大难题。如果一个普通的历史学家参与文艺理论界最近所发生的争论,特别是就一个文本的真正或基本内涵是存在于其创作者的内心,还是存在于著作本身(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展现出它的内涵),抑或是存在于其读者的反应之中,这样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话,那他将是愚蠢的。同样地,我们尽可不必怀疑接受理论(将之视为一个时间过程)对文化史学家著作的一般适用性和对书籍史学家们的特殊适用性。
插图目录
前言与致谢
第一章 传统与接受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廷臣?
第三章 《廷臣》在意大利
第四章 《廷臣》的译本
第五章 被模仿的《廷臣》
第六章 被批评的《廷臣》
第七章 复兴的《廷臣》
第八章 欧洲文化中的《廷臣》
附录一 1528—1850 年间的?廷臣?版本
附录二 1700 年前《廷臣》的读者名单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